以眼还眼:犯罪的惩罚简史.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4月13日
 |
| 第1页 |
 |
| 第6页 |
 |
| 第20页 |
 |
| 第30页 |
 |
| 第32页 |
 |
| 第241页 |
参见附件(2486KB,362页)。
以眼还眼:犯罪的惩罚简史,这是一本介绍犯罪史的籍,书中一共分为了九大章节来介绍内容,作者根据故事与现实内容进行编著,非常精彩!

内容提要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与暴力、欺骗、骚乱相伴而行。但对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何为罪?”,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历史阶段,会给我们相异,甚至相反的解答。而同一种罪行,惩罚的手段、性质及目的,也截然不同。从街头涂鸦到性侵,从连环杀人到公海劫掠及有组织犯罪,《以眼还眼》穿梭于人类历史的隐秘角落,探索对于犯罪的界定及惩戒。立足于不同文明的横览视角,加之以历史文明演进的纵览视角,最终勾勒出全球化视角下罪与罚的当代图景。
米切尔·P.罗斯不仅提醒了我们,在各地区密切交流前,某些罪行及惩罚为人类所共通,还试图向我们证明,原始部落的刑罚并不总比现代方式残酷。相反,在应对现代性问题时,一些传统的刑罚方式可能给我们启发。对比单独监禁,致力于恢复受害者、施害者及社群联系的“修复性司法”可能会更为经济,效果更好。此外,作者讨论了肉刑、囚禁、死刑等种种刑罚的变化与演进,为其在不同地区的废立,做了令人信服的阐释。
该书作者简介
米切尔·P. 罗斯(Mitchel P. Roth),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博士,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犯罪学教授,他的研究主要关注刑事司法的历史面向,以及谋杀、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的历史,著有《有组织犯罪》(Organized Crime)及《罪与罚:刑事司法制度的历史》(Crime and Punishment: A History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等书。他本人及研究成果也被CNN、FOX等多家媒体报导。
图书目录预览
第一章 罪与罚:太初
第二章 法律传统的兴起
第三章 变化中的犯罪:从封建制度到城市和国家
第四章 惩罚的转变与监狱的兴起
第五章 路匪、土匪、强盗和绿林好汉:贼帮和早期有组织犯罪
第六章 禁令、海盗、奴隶贩子、毒品走私犯和犯罪全球化
第七章 现代谋杀
第八章 后殖民社会的罪与罚
第九章 21世纪的罪与罚
以眼还眼:犯罪的惩罚简史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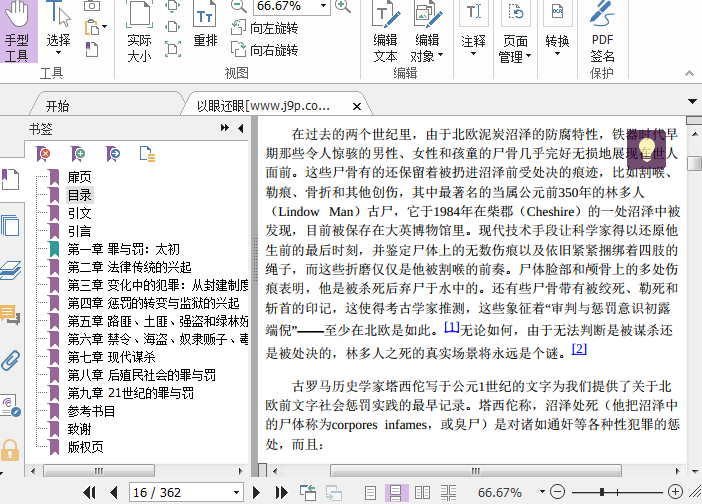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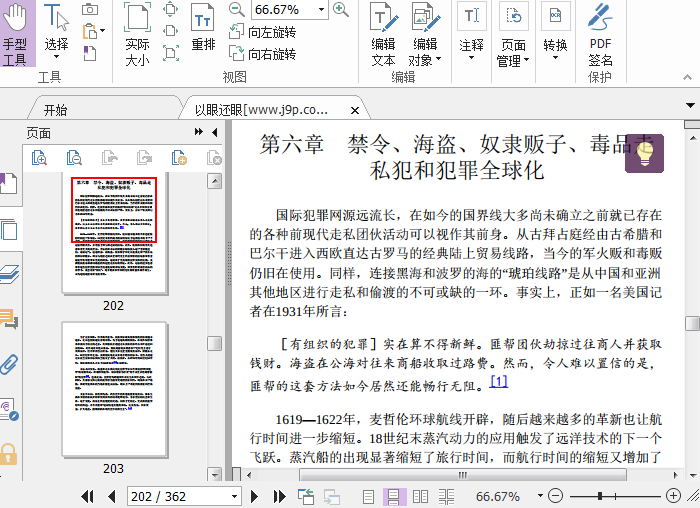
以眼还眼:犯罪与惩罚简史
[美]米切尔·P. 罗斯 著
胡萌琦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引文
引言
第一章 罪与罚:太初
第二章 法律传统的兴起
第三章 变化中的犯罪:从封建制度到城市和国家
第四章 惩罚的转变与监狱的兴起
第五章 路匪、土匪、强盗和绿林好汉:贼帮和早期有
组织犯罪
第六章 禁令、海盗、奴隶贩子、毒品走私犯和犯罪全
球化
第七章 现代谋杀
第八章 后殖民社会的罪与罚
第九章 21世纪的罪与罚
参考书目致谢
版权页引文
本书献给数千年来所有遭受
不公正的指控、审判和惩罚的人引言
往昔未逝,往昔犹存。
——威廉·福克纳,《修女安魂曲》,第一幕,第三场(1951年)
往昔俨然是另一个国度,彼时的人们行事古怪。
——莱斯利·珀斯·哈特利,《中间人》(1953年)
2006年,国际新闻界再次被几个监狱系统中的不寻常事件搅得沸沸
扬扬。你一定以为接下来会听到一个困顿绝望的悲惨故事。又有谁听说
过“令人愉悦”的监狱故事呢?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种反应是恰当的,毕竟,人们对监狱的认识——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如今的——总是同饥
饿、肮脏、混乱、暴力、堕落、帮派以及其他恶行画等号。不过,这一
次是一段被关在瑞典监狱里的三名以色列罪犯的极不寻常的小插曲。通
常,罪犯,尤其是被囚禁在海外的以色列罪犯,会寻求一切能从国外监
狱被遣送回国的机会。然而,当这三名罪犯面对如此安排时,却都以更
青睐北欧监狱的条件为由拒绝了,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牛排、性生活和播放世界杯的免费私人电视”。如果这些听上去还不够诱人的
话,那就再看看这些“五星酒店级”监狱的其他福利吧。首先是上面提到
的牛排、免费有线电视,以及为期三天并提供狱内豪华公寓的夫妻探访
日。此外,不仅每名罪犯享有独立房间,而且还有各种便利设施,每年
还可以(在警车的陪同下)在斯德哥尔摩逛两次街。[1]之所以选择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在微观层面上展现了同一时期、同
一类型的惩罚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里的差异。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发达
国家的前列。今时今日,处在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刑罚上尚且迥然有
别,若纵观古今,放眼全球,不同种类的犯罪与惩罚间的差异想必会更
明显。监狱和监禁概念在18世纪理性时代的出现,是全球犯罪与惩罚史
上的里程碑。能施加在人体上的痛苦纵然有其极限,对监禁的理解却在
全球范围内以各种形式继续发展和演变,且其发展和演变仅受限于资
金、技术和创造力。21世纪瑞典和以色列监狱的例子仅仅让我们对全球
犯罪与惩罚的故事有了匆匆一瞥。不过,我们会继续深入下去。
本书将带领读者展开一段间或令人不那么舒服的旅程,穿越罪与罚
的演变。这趟旅行恐怕并不适合时间旅行者,因为途中充满了古往今来
的斩首、绞刑、石刑和其他可怕的刑罚。研究特定国家、宗教、地区和
大陆的犯罪与惩罚史的佳作不在少数,但除了多卷本的参考书之外,还
没有哪本书试图从全球视角考察该话题。本书中的历史叙事则广泛考察
了数千年来罪与罚的发展。
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惩罚(在历史或书面记录中)被定义为一种通
常由国家施加给违法者的强制性处罚。在历史上,罪的概念曾与恶的概
念相伴相生。从恶行与善行的概念到罪行理论的形成,《圣经》、《古
兰经》和《摩西五经》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虽然罪与恶(违背道德法
则)皆被视作不可接受的行为,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罪通常是对成文法
的违反。随着处罚罪行的责任从神学权威转移至国家,神职人员被警察
取代,“恶似乎消失了,因为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和新的监控手
段”。[2]
“何为罪?”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通常的观点是将罪与恶,或
将罪与如今人们所说的反社会行为画上等号。但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及
结构连贯性考虑,我们在此将把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即是否违背法
律。读者会发现,一个社会的刑法主要着眼于该社会及其统治者的核心价值、道德和原则。事实上,在有些文化中,最初的文字记录或文学作
品正是以行为准则和法典的形式流传至今,且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惩罚条
款。将行为定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对罪行种类或个人罪行与国家暴
力的区分只有在相对成熟的社会中才适用,这一点已成共识。在史前社
会,罪犯由该地区的公众进行审判和惩罚,因为人们认为,罪犯的行为
危害了整个地区。放眼全球,社会与社会间千差万别,各个社会所定义
的罪行大相径庭,迄今犹是。本书基于过去20年对犯罪与惩罚史的关
注,薄薄一册,只不过是就该论题进行了跨越千年的综述,绝非综合性
的参考大全。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初期阶段的犯罪与惩罚状况,我们只能凭借假
想。人们已尝试在某些学科中通过对殖民时代前的传统文化的观察来进
行推断,并基于这些推断进行假设,从而解释晦暗不明的过往,弥合认
识的断层。在14世纪之前的英国,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谋杀和个人犯罪
的记录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认为,直到12世纪英国巡回法庭出现,国王
的法官才会定期在郡与郡之间巡视、记录犯罪活动的细节,对杀人罪和
其他罪行的系统研究方得以开展。[3]
随着书面资料的积累,罪与罚的历
史也自然变得更易梳理。之后,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不是单纯地收集点
滴素材,而是要对材料进行扬弃。
社会往往依照其文化信仰来设计惩罚的手段。例如,亚洲社会曾青
睐“其辱尤甚于死”的公开惩罚。没有哪种形式的死亡比死后还要被分尸
更可怕。人们相信,躯体完好无缺地入土为安,灵魂才能顺利升天,因
此斩首(通常还伴随其他形式的肢体破坏)便被视作极端的惩罚手段。
与媒体哗众取宠的报道以及流行文化对连环杀手、杀人狂的渲染相
反,长期的证据表明,我们的世界事实上正变得更加安全。[4]
自文明伊
始,人类似乎就展现出相互伤害的倾向,并发明了各种新奇手段来惩罚
那些违反社会行为标准的人。每种文化都形成了其对犯罪与惩罚的理
解。千年来,人们对恶行的反应惊人的一致,所不同的仅是受到技术与想象力的制约。早在成文法创立之前,人类社会就已有了规矩和习俗,以便维持秩序,形成约束,使社会免受犯罪者危害。研究者对这一时期
的称呼各有不同,但都尽力避免使用“原始”之类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
学者在精神上更加中立,也不那么武断,他们更喜欢用更得体的词语,比如“史前的”“部落的”“无文字社会的”“前殖民时期的”等等。随后的关
键所在就是考察各个社会如何定罪并制定相应的惩罚。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对罪与罚的态度变化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棱镜,它折射出人类的进
步。
罪与罚的历史不断发展,新的发现总是不断打破业已被认可的观
点。想象一下,在1901年《汉穆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被
发现之前,我们对巴比伦法律的理解,或者想象一下在1799年之前、为
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带来巨大突破的罗塞达碑(Rosetta Stone)尚未
被发现之前的埃及学。书写任何一种“全球史”都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
类活动根本没有书面记载。即便在21世纪,从人口稠密的地区获取有价
值的罪与罚的数据也绝非易事。因此,从诸如中国、越南、朝鲜、沙特
阿拉伯、苏丹和古巴等国收集有价值的犯罪数据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得
考虑从前文字时代追寻原始记录、建立历史档案所要面临的挑战。当你
对不透明的社会或专制政体下的罪与罚进行考量时,今昔有时也变成了
如往昔那般的“陌生国度”,成了令人沮丧的密码。因此,在涉及大时间
跨度的全球编年史时,无论何种题材,研究者往往都不得不借助推断、演绎和猜测。不过,我们也可以求助于民间传说、口述历史、传闻逸
事、神话和古典文学,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它们有时能带来意
外收获,以填补历史和史前记录的空缺。
当人们提起监狱和罚金、绞刑架和断头台、砍头或鞭刑时,指的无
疑是各种各样的惩罚手段。然而,说到犯罪本身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同
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未必都会被视作犯罪。众所周知,宗教国家严
禁通奸、淫乱、亵渎神明、滥引主名、叛教和其他犯罪行为。但如果绝
大多数世俗国家并不禁止上述行为,对于通奸在美国24个州仍是一种犯罪,这一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呢?
关于全球犯罪与惩罚的许多基本理论并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例
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罪犯的惩处渐渐从体罚向经济补偿和监禁转
变。但纵观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事实最为普遍,即受害者和犯
罪者的地位是确定判决结果与量刑的主要因素。从远古时代到封建时
代,再到如今,当人们需要同司法体系打交道时,特权阶层的身份总是
有利的。自第一部成文法典起,法律就已为富人所独享。《汉穆拉比法
典》明确规定,对低等阶层的惩罚最为严厉,律法之下完全没有平等可
言。在印度的大多数普通犯罪事件中,如果受害者是平民或低种姓人,那么富有的罪犯将受较轻的刑罚,支付较少的罚金。依社会地位定刑的
做法可以从印度古老的《摩奴法典》(Laws of Manu)、菲律宾的伊富
高人(Ifugao)以及中国的唐朝找到踪迹。不过,总是不乏奇怪的例
外,比方说,阿兹特克人认为贵族理应品行更端,因此倘若贵族违法,就会受到比平民更严厉的惩罚。此外,还有一些经久不变之处,比方
说,数世纪以来,罪犯,尤其是暴力犯,绝大多数是年轻男性。与此相
应,最残酷的惩罚也落在了男性的头上。例如,在英国历史上,从没有
女性被处以绞刑。
纵观史料,罪与罚发展中的另一种模式是对更人道的处决方式的不
懈寻求。从雅典人使用的毒芹和斩首,到断头台、电椅和毒气室的技术
奇迹,最后(截至目前)是注射死刑,刑罚改革者在决定如何处决我们
之中的败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代社会甚至还给一些如今仍在
使用的原始惩罚方式添加了新意。以往,罪犯在见刽子手之前并没有什
么准备,但在现代化的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死刑犯常常在被送往公共广
场斩首前注射镇静剂。在伊斯兰国家,那些面临削手削足刑罚的人也会
事先被注射适量麻醉剂。
采用全球视角的历史性叙事方式,不仅是要论证某些犯罪与惩罚的
普遍性,也是要试图让读者意识到,原始的惩罚手段并不比现代方式残酷。的确,刑罚是残酷无情、疏而不漏的,但总体而言,比起仅仅几个
世纪前还在西方使用的轮刑、火刑或开膛破肚,古代部落的刑罚要温和
得多。
所有历史作品,尤其是那些试图采用全球化视角的作品,都受制于
内容与长度、内涵与外延,本书亦不例外。我在此类或彼类罪行、此类
或彼类刑罚中反复斟酌,孰取孰舍取决于该类罪行是否与专门的成文法
相对应。固然,全球史可以涉及诸如战俘营与集中营、种族灭绝、恐怖
主义、宗教战争、种族和政治团体、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其他反异端宗
教运动等论题,但上述内容都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围。
涉及犯罪与惩罚的史料里不常出现儿童和女性。正如上文提及的,大多数罪行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年轻男性所犯。至于女性犯罪,我们会发
现,越向久远回溯,她们就越频繁地出现在巫术、通奸和杀婴之类“特
定性别”的案件中。由于儿童在司法体系中没有主体地位,提及他们的
史料便更少。本书下文对罪与罚的讨论着眼于不同文化中最具时间连续
性的部分。例如,虽然有若干书籍对绑架专门进行了探讨,但此类罪行
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不过,就全球犯罪与惩罚史而言,犯罪行为的
理论基础这一论题却是相当新的。例如,直到1874年查理·罗斯案
(Charley Ross case)之前,绑架在美国尚未成为“成熟的公共话
题”。[5]
另一个值得花整本书的笔墨进行探讨的问题是金融犯罪史。作为21
世纪(截至目前)的标志性犯罪,经济犯罪自第一批铸币诞生、第一次
税收令颁布、第一次金融犯罪行为出现以来便与我们如影随形。在大部
分历史文献中,金融犯罪指涉的是伪造货币、走私、逃税、行贿受贿等
等。但如今,当人们谈到这个话题时,主要想到的却是伯纳德·L.麦道夫
(Bernard L.Mado)案那种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诈骗案。新技术为行骗者
提供了难以置信的便利手段。自从17世纪商业迅速扩张以来,骗子横行
的状况已司空见惯,但彼时的骗子尚不足以成为危害全人类的毒瘤,因此也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
为了给犯罪与惩罚这对不可分割的话题组织起既广泛又有趣的素
材,作者深入挖掘了各国史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以往相关的书籍
主要以西方为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西方社会的原始素材更
多。本书试图拓展该研究领域,关注那些不为人所熟知、较少被载入史
册,因而其罪与罚的状况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历史性讨论的地方。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我选取了大量富于启发性的话题、事件和故事,以便提供
某种时间上的推动力和连贯性。
第一章带领读者领略从史前到古代社会的刑法和惩罚。在陪审团、监狱和法庭系统出现之前,相比成文法,前文字社会的文化更依赖于不
成文的习俗。在对近东地区、埃及、印度、中国和其他地区最早的成文
法典进行探索之前,本章将先考察我们对这些文化已有的认知。
第二章考察了各种有影响力的法律传统的发展。回溯史料,诸多法
律传统起落兴衰,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四种法律传统。至今有的法律体系
依旧存在,比如伊斯兰法律传统、普通法传统、民法传统和社会主义法
律传统,而更多的法律传统则或消失或融入某种混合体系。由于欧洲殖
民势力在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将普通法传统和民法传统传遍全球,所
以本章将重点关注这二者。
第三章考察了罪与罚在不同社会进入国家体制进程中的发展。本章
论述了在集权官僚体制兴起和威权建立之前封建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
为了征税、制定法律、保持和平所进行的司法实践。封建社会在日本和
西欧这两个迥然有别的地区都昌盛一时,直到19世纪,该体制依旧是维
系社会的重要力量。
第四章论述了惩罚的转型和现代监禁制度的发展。这个话题至关重
要,因为一个国家的惩罚方式可以向我们展现出一个国家的面貌及其文
明化程度。虽然各国对监禁的采用情况不尽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抛弃公开死刑和体罚,转而使用监禁作为惩罚手段。
第五章阐述了在犯罪全球化之前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直到19世纪,犯罪主要还是地区性行为。早期犯罪团伙往往出现在政府孱弱、警察无
能、民众分化的地方。几乎在每个国家里,各类非法团伙都惊人地层出
不穷。有些最早的记录来自亚洲,如13世纪日本带有幕府色彩的恶党
或“恶帮”。从印度土匪、苏格兰强盗到墨西哥银帮、巴西游击队,以及
其他各种各样的“亡命徒”形象,人们对亡命徒的印象可谓五花八门。欧
洲甚至还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盗贼。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只活跃于
能得到某些民众支持的地区,通常是在乡村。此外,一旦政府的组织更
有效或警力更充足,他们便好景不长。直到组织更严密的犯罪团伙——
奴隶贩子、海盗和贩毒集团——的兴起,同时伴随着运输、通信手段的
进步以及因全球各地不同禁令而产生的机会,犯罪活动才开始超越国
界。
第六章在前一章聚焦地区性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追
寻了国际犯罪团伙的根源。全球化发展促进了交通运输的改善和通信的
进步,加之一些考虑不周的商业禁令的通过,刺激了跨国犯罪团伙的兴
起,并令其得以继续危害现代社会。
第七章探究了谋杀的历史,重点关注多重谋杀和与性相关的谋杀形
式。诚然,本章也可着眼于抢劫、强奸、贿赂和其他活跃了数个世纪的
种种罪行,但没有哪种罪行能比始终被人们大书特书的谋杀更具代表
性。从古希腊文学和《圣经》,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再到当下流行的犯
罪纪实文学,谋杀一直是世界文学界的热门主题。尽管我们人类在科学
和文化上取得了进步,但我们仍然以惊人的速度自相残杀。据估计,20
世纪,有100多万名美国人被谋杀(不包括战争中的受害者)。人类历
史有多久远,谋杀的历史就有多久远。一个多世纪以前,弗雷德里克·
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曾说:“如果一个仙女给他机
会,让他亲自见证各个社会中的同样类型的场景,他会选择谋杀审判,因为它揭示了首要之事的方方面面。”[6]
一名犯罪历史学家甚至认
为,“谋杀”这个词在日常用语中最为重要。与亵渎神明、过失杀人、弑
君和恋童癖等罪行不同,当提到“谋杀”这个词的时候,任何人都明白那
指的是夺人性命。正如历史学家罗杰·莱恩(Roger Lane)所言:“事实
上,谋杀是最容易深究其历史的一种罪行:总是受到认真对待,总是有
法可依,且从未变得稀松平常以至于被人们容忍或忽视。”[7]
被研究最
多的一类谋杀大约是连环谋杀。在大众的观念中,连环谋杀是一种现代
现象,但事实相反,有证据表明,连环杀手自古有之。只要看看童话故
事、魔法故事和数世纪以来关于狼人和吸血鬼的记载,就可略知一二。
从非洲到西欧,各式各样豹人、狼人之类的故事很可能是从现代警察和
法医调查尚不存在的迷信时代的真实分尸凶杀案中得到了灵感。
第八章探讨了殖民主义和其他政权的建立过程在惩罚的全球化传播
中所扮演的角色。彼此相邻的国家,其罪与罚的理念往往相似。在相对
孤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埃及,其罪与罚的观念则往往
有天壤之别。但就罪与罚的理念传播而言,最强有力的途径之一莫过于
欧洲殖民主义进程。数个世纪以来,世界强国在全球建立了殖民地,一
方面传播他们的刑罚理念,一方面吸收借鉴当地的传统。此后,当这些
殖民地、海外领地和受保护国纷纷独立建国,它们的许多刑罚理念都是
建立在本土和殖民时期惩罚实践的基础上的。
第九章是这段漫长罪与罚之旅的终点。本章展示了罪与罚的循环,以及古代和现代犯罪行为之间显著的连续性。在高科技犯罪日益发展和
增多的同时,诸如亵渎神明、信奉异端邪说、通奸、海盗和巫术等古老
的罪行依旧长盛不衰,处决、耻刑、流放等古老的刑罚也相伴而存。此
外,本章也指出,当涉及犯罪与惩罚时,一个社会往往会求助于历史资
料,从过往的犯罪控制经验中寻找策略,同时对先前严重依赖死刑和监
禁的惩罚制度提出质疑。
罪与罚的全球史表明,尽管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辉煌的进步,但人们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对该行为的相应惩罚有着明显的延续
性。在数字化的后工业时代,虽然犯罪手段日新月异,但犯罪目的和动
机以及审判体系与早先的差异并不大。归根结底,本书表明,罪与罚的
历史乃是一部反复无常的实践史——借鉴、吸收、寻找新的替代品,司
刑者往往回到故纸堆中,向当前的新世界重新祭出古老的惩罚手段。虽
然关于上述现象的证据并不充足,但在过去几十年间,人们的确看到,行耻刑、用锁链将罪犯锁在一起,以及公开行刑等旧式处罚方式已死灰
复燃。
[1]Itamar Eichner,‘Israelis Enjoying Life in Swedish Prison’,www.ynetnews.com,12June2006.
[2]Karl Menninger,MD,Whatever Became of Sin?(New York,1973),p.50.
[3]James Buchanan Given,Society and Homicide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Stanford,CA,1977).
[4]参见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trans.E.Jephcott(Oxford,1978);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le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New York,2011);Manuel Eisner,‘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Crime and Justice:A Review of Research,xxx(2003),pp.83~142。
[5]Paula S.Fass,Kidnapped:Child Abduction in America(New York,1997),p.10.“绑架”这个说法
源自“窃贼”一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该词是由“孩子”(kid)和“攫取”(nap)组合
而成。
[6]Pieter Spierenburg,A History of Murder:Personal Violence in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Cambridge,2010),p.1.
[7]Roger Lane,Murder in America:A History(Columbus,OH,1997),pp.1~5.第一章 罪与罚:太初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于北欧泥炭沼泽的防腐特性,铁器时代早
期那些令人惊骇的男性、女性和孩童的尸骨几乎完好无损地展现在世人
面前。这些尸骨有的还保留着被扔进沼泽前受处决的痕迹,比如割喉、勒痕、骨折和其他创伤,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公元前350年的林多人
(Lindow Man)古尸,它于1984年在柴郡(Cheshire)的一处沼泽中被
发现,目前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现代技术手段让科学家得以还原他
生前的最后时刻,并鉴定尸体上的无数伤痕以及依旧紧紧捆绑着四肢的
绳子,而这些折磨仅仅是他被割喉的前奏。尸体脸部和颅骨上的多处伤
痕表明,他是被杀死后弃尸于水中的。还有些尸骨带有被绞死、勒死和
斩首的印记,这使得考古学家推测,这些象征着“审判与惩罚意识初露
端倪”——至少在北欧是如此。[1]
无论如何,由于无法判断是被谋杀还
是被处决的,林多人之死的真实场景将永远是个谜。[2]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于公元1世纪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北
欧前文字社会惩罚实践的最早记录。塔西佗称,沼泽处死(他把沼泽中
的尸体称为corpores infames,或臭尸)是对诸如通奸等各种性犯罪的惩
处,而且:
具体的处罚方式依罪行而异。叛徒和逃兵被吊死在树上;懦夫、逃
兵和鸡奸者被塞进藤条笼里浸入泥泞的沼泽中。惩罚手段的区别是基于
这样的理念:背叛国家的人应当被拿来杀鸡儆猴,而做出不齿行为的人
则应从公众的眼前消失。
但此处的关键词依旧是“可能”,因为尽管有这些我们自认为已掌握
的关于前文字时期的知识和古代历史学家的叙述,在沼泽尸骨究竟是惩罚、祭祀神灵的结果,抑或二者皆是的问题上,我们仍未能达成共
识。[3]
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并不是自然死亡。
自古以来,人类似乎就已经有了制造骚乱并对制造骚乱者实施千奇
百怪的惩罚手段的本能。事实上,暴力和同情似乎常常在我们体内共
存。关于此类行为的最早书面证据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古代中东地
区。不过,人类的历史要比那久远得多。
某些秩序理念在各种文明中都发挥了稳固作用,比如我们不可否
认,为了更广泛的社会的利益,个体的冲动必须以某种形式加以约束。
各路权威声称,法律只存在于有法庭体系且法律条文能得到政治组织结
构化的国家支持的地方;但前国家时期的文明极少拥有这种意义上的法
律。然而,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他人恶意伤害的规则却比比皆是。就此意
义而言,大多数前文字时代中的确存在法律。不过,这些法律之间有着
天壤之别。早期人类社会形态各异,其习俗和信仰体系也千差万别。正
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言:“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远古法律’,一如不存
在天下大同的原始社会。”[4]
尽管如此,每个文明都为管理和规范行为
制定了规则。
在文字出现之前,当时的人们将我们所谓的“罪行”或“恶行”与那些
极有可能令诸神迁怒于族群的行为——那些被认为有害于整个社群的行
为——等同视之。例如,在非洲阿善提部落的人眼中,罪即是恶,指的
是“令族人厌恶”或不仅冒犯部落祖先神灵,也极有可能为整个部族招来
神明之怒的行为。因此,部落首领要惩戒作恶者,否则族人将遭受祖先
怒火的惩罚。[5]
我们已有的或自认为已有的关于前文字时代罪与罚的知识,大多是
基于推测,基于人类学、人种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但没有书面记录,任
何发现都不尽准确,只能纯然仰赖口述历史和对现存游牧和狩猎采集者
群体的观察。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萨瑟兰·拉特雷(Robert SutherlandRattray)在20世纪初研究非洲阿善提社会时,认为那些人是“和平的”,在他们中见不到任何积怨仇杀的痕迹,部族的惩罚体系掌握在法官、酋
长和国王等高级领导者手中。他颇为自信地推测,地位越高的阿善提人
受到的惩罚越严厉,这“可能与早期正义背道而驰”[6]。“可能”一词在此
不可或缺,因为没有记录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有根据的猜想。拉特雷对
过往的诠释至多不过是考察了欧洲人到达之前的阿善提文明。他最惊人
的断言之一是,最严厉的制裁似乎是“嘲笑的力量”。通观他的研究以及
对口述传统的考察,他发现人们对嘲笑的恐惧始终存在,也就是
说,“与这种笑里藏刀、剥夺了一个人的自尊和被周围人尊重的武器相
比,即便最残酷的惩罚也未必更可怕”。阿善提人有句谚语:“若要在耻
辱与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则宁可选择死亡。”这种信念在一则小故事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名乡村长者向来访的显要人物躬身致敬,却“无意
间放了一个屁”。不到一小时,长者回到家中悬梁自尽。当有人怀疑此
长者的极端反应乃是由于精神错乱时,他的部落兄弟们却一致认为他在
这种情况下做了恰当的事。[7]
由于口述传统以及由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拉特雷所做的研究,我们有了一些阐释早期阿善提人罪与罚传统的基础。最常见的死刑行刑
方式是用小刀斩首。行刑者要抓住受刑者,从脖颈处由前向后切割。但
行刑者“若不愿直面受刑者的脸”,务实的阿善提传统也允许行刑者按住
受刑者的头部,“从脖颈后方切割”。其他方式包括用皮绳或徒手扼死,以及用大头棒打死。[8]
此外,某些残肢手段也可以作为处罚。若受刑人
被认为犯了不敬之罪,可能会被割掉整只(或部分)右耳。有一则广为
流传的故事可为我们提供佐证。故事中说,一名男子被判用一只绵羊作
为对冒犯他人行为的赔偿,该男子却回答说,用一头牛更合适,尽管他
很清楚牛这种动物不为本族群所容。结果,他被割掉了双耳。在其他情
况下,那些被控做伪证或出口伤人的人会被割掉嘴唇;割鼻适用于对傲
慢无礼或自我夸耀、飞扬跋扈者的惩罚。[9]
宫刑是专门用于惩罚那些不
经意间窥见了首领的裸妻的宫廷侍者,因此,侍者往往要在进入宫闱时高呼“嗖嚯,嗖嚯”,以宣告自己的到来。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刑罚,但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直到欧洲人到来之前,在除谋杀罪之外的特定情况
下,当地人可以通过“买人头”(支付罚金)的方式免于被处决。被判死
刑的孕妇会被拴在木桩上等待分娩,之后,母亲和婴儿都会被处死。后
来,在阿善提建立殖民地的英国人也允许被判刑的女囚在被处决前分
娩,以此彰显其文明。二者相比,唯一不同的是,后一种情况下出生的
孩子会被收养。
说到罪与罚,几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实际上,“似乎并
不存在绝对一致的人类良知”,至少,历史学家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是这么认为的。[10]
不过,乱伦似乎在全世界都被视作不可容
忍的犯罪行为。在史前社会中,血缘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牢不可破的纽
带,这意味着早在史前时代之初,乱伦的禁忌便存在于几乎所有文明
中。乱伦属于要被判死刑的性案。阿善提人认为乱伦的行为罪可处死,并视之为mogyadie,即“饮自己的血”。但是,他们所谓的乱伦,其含义
较之现代意义要宽泛得多,它囊括了与任何属于同一血缘或氏族的人发
生性关系,无论两人的关系亲疏,只要他们的姓氏相同,就足以被双双
处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最为人所唾弃的恶行。
至于通奸,尽管往往仅在女性为过错方时才会进行惩处,却并不像
乱伦那样具有普世规则。最早的成文法对通奸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汉穆拉比法典》、《希伯来法典》和后来的古希腊法典均规定,犯通
奸罪的女性将被处死。值得指出的是,在汉穆拉比统治时期(约前1792
年—前1750年),巴比伦的居民可能实行某种形式的祖先崇拜,而通奸
行为会危害或削弱血统,因而被视为亵渎之罪。在现今留存的近东地区
最早的关于通奸的法律中,规定了旨在约束家庭成员关系的残酷惩罚。
在通奸问题上,丈夫可以决定是处死妻子及其情夫还是将他们双双致
残。如果是后者,则妻子可能会被割鼻,其情人会被阉割和毁容。在今
天的喀麦隆,图普里部落的通奸妇女必须终生佩戴铜圈;在美洲原住民
黑脚人中,若妇女通奸被丈夫当场抓获,就不得不立刻接受割鼻的惩罚。
在一些部落文化中,各类杀人行为,无论是事出偶然还是蓄意为
之,因令统治者失去了臣民,故均被视作犯罪。[11]
与西方法律不同,乌干达塞贝人的法律规定,杀害近亲不算谋杀。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
必须意识到,在此,家族是个法律实体,且他们尊重杀戮。在这种情况
下,家族首领会表现得相当务实。一名研究过塞贝人的人类学家记得这
样一个案例:家族首领认为,“一个生命已经被毁灭了,我们不能让家
族一下子失去两个人。死者是坏人,死有余辜”。一些非洲部落社会,比如非洲西南部的班图部落,对过失杀人和意外伤害做出了区分;而菲
律宾的伊富高部落则对故意、过失和意外行为做出了严格区分。在一些
美洲原住民平原文化中,对杀人的惩罚是四年的流放。在此期间,杀人
凶手被要求留在营地周围,并不得与除直系亲属外的任何人接触,而他
的直系亲属则被获准为他提供食物。惩罚期的长短取决于受害者亲属的
态度,因为只要他们同意,杀人凶手就可结束流放。[12]
波尼人部落很
少以命偿命,而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波瓦坦部落(Powhatan
Confederacy)则把杀人视为对部落的冒犯,要求以酋长的名义处决触犯
者。荣誉杀戮、仇杀、赔偿和赎罪金
为荣誉之故而实施的犯罪如今在世界很多地方依旧常见。但若论此
传统的传承,没有哪里能比地中海地区更强。早在公元前400年,该地
区的丈夫就可以合法地杀死有通奸行为的妻子(以及情人)。时光飞逝
2400年,到了20世纪,意大利刑法第587条规定,若被戴绿帽子的丈夫
(或愤怒的父亲、兄弟)杀了出轨的妻子(或女儿、姐妹)或她的情
人,只需在狱中服刑3~7年。与此类似,黎巴嫩刑法第562条允许男性杀
死因性行为“给家族蒙羞”的女性亲属。20世纪70年代,一个妇女团体试
图推翻这条规定,但身为基督徒的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Suleiman
Frangieh)回应说:“不要触碰荣誉。”作为对这句话的行动响应,他在
一名男子勒死其与人调情的女儿仅仅9个月之后便赦免了该男子。直到
20世纪,维护荣誉这个理由仍在美国至少3个州得到认可,包括得克萨
斯州。仅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圣保罗就有722名男子使用了维护荣誉
这个理由,直到1991年该理由被取缔。值得一提的是,在拉丁美洲,为
维护荣誉而犯罪的理念只是几个世纪前众多输入新大陆的殖民文化观念
之一。
人类在早期社会就已意识到通过禁止氏族宿仇升级来维护秩序的重
要性。其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规定只有由受害方家庭的一名成
员对侵害人本人实施的杀戮或残肢行为才是被许可的复仇,且复仇行动
应止于此。至此,侵害者的家庭与仇杀不再相干,并已向受害者家庭偿
清了债务。早期法律体系中最常见的理念之一是用赎罪金或赔偿代替复
仇。《汉穆拉比法典》和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法律以及《旧约》(尤其是
《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都包含了赔偿条款(后来的伊斯兰律法亦
然)。赎罪金在日耳曼法律中同样极为常见,且男系亲属负有偿付责
任。赔偿制度在盎格鲁-撒克逊司法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约1500
年前的《埃塞尔伯特法典》(Laws of Ethelbert)中罗列了对各类伤害的具体赔偿细则。
赎罪金在伊斯兰律法中由来已久(见第二章)。即便是在今日的巴
基斯坦,因杀戮引发的纷争也依旧可以通过受害者的继承人与侵害者之
间达成赔偿协议的方式实现庭外调解。前者必须宽恕,后者必须支付赔
偿。中央情报局(CIA)探员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经历的
一起案件足以说明这一点。戴维斯称自己杀死两名巴基斯坦人是出于自
卫需要,但仍旧遭到了逮捕。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表示,可以通过向死
者家属支付赎金的方式了结此案。[13]
几个世纪以来,即便在那些家族仇恨可以逾越法律而得到认可的地
方,往往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直到20世纪,阿尔巴尼亚的刺客仍应
在行刺之前警示受害人,且永远不得从背后下手。一旦刺杀成功,要将
尸体以仰卧姿态放置,且任何人不得劫掠尸体。另一些规定禁止在市场
或繁忙的道路上袭击牧羊人或实施谋杀。在阿尔巴尼亚,当家族仇恨涉
及的任何一方想种田、举行聚会或做生意时,可以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暂时搁置复仇。死者家属被允许在凶杀发生的24小时内向凶手或其任何
亲属寻仇,24小时之后则只能对凶手本人实施报复。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大量证据表明,很多文明都认可用某种形式的
物质补偿来避免愤怒的受害人家属或亲族实施报复。但亦有大量资料表
明,各个文明对于何种罪行可以用赔偿方式解决意见不一。例如,伊富
高人的习惯法(来自菲律宾吕宋岛)允许除故意杀人罪之外的几乎所有
罪行适用赔偿代责,对故意杀人罪则必须血债血偿。
在其他承认集体责任的文化(意味着犯罪者的亲族也有责任)中,某个家族成员被杀会引发家族世仇。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的原住民采
用“合法对抗”的方式来避免上述情况。“合法对抗”的一方是持盾的罪
犯,另一方是被害人的亲属或近邻。被害人的亲朋好友可以向凶手投掷
长矛,凶手则全力躲避。一旦凶手受伤流血,无论是死是活,对抗(以及双方未来的冲突)即宣告结束。与后来那种用折磨手段判定有罪或无
辜的审判不同,这里提到的凶手首先须是已确定有罪之人。
在另一些文明中,比如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对于伤害、偷盗、毁
坏财物或用不齿手段诱拐他人妻子的事件,会编出讽刺歌曲来嘲笑犯罪
者,“夸张地嘲弄他们,甚至抖搂出对方的陈年家丑”。受嘲弄的人可以
用同样方法做出回应,但最关键的是没有明显的肢体冲突。不过,如果
涉及凶杀,罪犯的麻烦就大了,因为受害人的近亲可以用相似的手段报
复加害者或其近亲。集体责任的观念有可能在无意间将仇恨传给下一
代,导致众多无辜生命的逝去。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述:“在人们试图惩
罚凶手之前,罪行或许已过去很多年,而在此期间,凶手或许曾拜访受
害者的近亲,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款待,平静地生活了很久。然后,他可
能会突然被同伴派去参加狩猎活动或摔跤比赛,且如果不能取胜就要被
处死。”[14]
某些南非部落,比如祖鲁族(Zulu)和科萨族(Xhosa),让我们
看到了部落刑法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公正掌握在部族首领手中,因为按
照传统,所有族人都属于他。因此,他也要对受害人的一切损失做出补
偿。一名男性值7头牛,一名女性值10头牛(差别在于女性出嫁时可以
获得的彩礼)。1820年之前,丈夫可以杀死奸夫且免受惩处。在大多数
情况下,对罪行的处罚以罚金为主。
从古到今,复仇一直是惩罚体系背后的驱动力。近年来发生在拉丁
美洲、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案件一次又一次表明,农业社会的人倾向
于以正义的名义自行执法。2003年6月11日,墨西哥拉坎德拉里亚村
(La Candelaria)的村长在遭绑架和谋杀后被埋葬。村民迅速围捕了四
名嫌疑人,用私刑处死了其中两人,听任另外两人慢慢等死。被制度腐
败和镇压激怒的当地居民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行使了超越法律的公
正,这让一名观察者认为“恰帕斯(Chiapas)从来不存在法律制度”,并
说“当人们无法获得公正时,就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境况中,[且]公正由那些实施公正的人来定义”。2002年,早在如今的贩毒集团火拼之
前,私刑在墨西哥不少原住民居住的地区相当常见。很多杀戮都是由家
族仇恨和世仇所致。警方则认为“印第安人杀印第安人不足为奇”,不愿
介入,以免“打破村庄内部以及村与村之间脆弱的力量平衡,而这种力
量平衡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该地区的秩序”。[15]
时隔两年,玻利维亚的一名镇长被粗暴地吊在灯柱上焚烧。当绳子
系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已经被殴打致死。当地居民在实施此次私刑处
决前曾经历了一场并不成功的法律诉讼。他们向玻利维亚财政部、参议
院和法庭控诉有人侵吞了本应用于贫苦村民的数十万美元政府资金,但
均以败诉告终。饱受欺压的阿尤阿尤村(Ayo Ayo)的镇长之死被人们
普遍视为“群体正义行为”,这种行为在拉巴斯(La Paz)以南一小时车
程的小山地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正如一名观察者指出,镇长被
杀“是因为他是令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贫苦无助的不公正制度的一部分”。
用一名农民的话说,那些统治国家的白人和混血儿精英“也该落得同样
下场,如果不被烧死,就该被淹死、绞死或者四马分尸”。这个观点受
到了一名社会学家的支持,他将私刑处死看成是“对普遍视作服务于富
人和权贵利益的司法体系的拒斥”。无论如何,这种死亡惩罚只有在整
个社群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极端情况下才会被使用。[16]《汉穆拉比法典》
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发掘
出《汉穆拉比法典》,这是一块8英尺[17]
高的黑色玄武岩石板,上面刻
有4000行楔形文字。[18]
此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环境
宜居,早在约5000年前就已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组织。这部法典后来进一
步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的刑罚程序,但其法条只在与近东地区接触后才
会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
大量证据表明,新月沃地较早的法典在汉穆拉比之前约300年就形
成了罚款和赔偿制度,可追溯到第三乌尔王朝的建立者乌尔纳姆(Ur-
Nammu,约前2111年—前2095年在位);那部法典中的部分措辞也被
挪用到了《汉穆拉比法典》中。不过,令《汉穆拉比法典》卓然于世的
是,它首次提出了“以眼还眼”的原则。与早前依靠罚款和各种补偿手段
的法典不同,《汉穆拉比法典》引入了复仇的概念,被认为是第一次试
图控制私人复仇行为。这部复仇之法从字面上看是一种问责制。比方
说,如果一座房屋倒塌并导致屋主的儿子死亡,要偿命的不是造屋者,而是造屋者的儿子。不过,如果在房屋倒塌事故中丧生的是一名奴隶,造屋者只需向受损者赔偿另一名奴隶即可。另一则条款规定,“如果一
名男子攻击了一名女性自由民并导致她流产,则该男子应赔偿她10谢克
尔的损失”。但如果该女性死亡,则行凶者的女儿就会被处死。与此类
似,趁火打劫的人会被投入火中。这些法律的影响力在近东地区的历史
上显而易见。1903年的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年代稍晚的、刻在一系列陶土
碑上的亚述法典用楔形文字重申着同样的理念:“如果有女性在与男性
市民的打斗中打碎了后者的一个睾丸,则要被判截去一根手指,如果经
过治疗,另一个睾丸也破碎了,则要被判弄瞎双眼。”直到1999年,巴
基斯坦法律仍规定,被害身亡者的家庭成员可以用该凶手作案的手法杀死已被定罪的凶手(也可以慈悲为怀)。一个用扼杀、肢解、溶尸的手
段杀害了100名儿童的连环杀手被判以同样的方式处决,便是很好的证
明。
大体而言,《汉穆拉比法典》共有282条,每一条都体现了国王的
一项革新。法典不是一套完整的法律,而是设立了分别针对巴比伦社会
三个等级民众的一系列惩罚措施。但它的缺憾在于,它没有编纂新的法
律体系,既不指导法律程序,也不告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19]
法典规定的惩罚是严酷的,但相比距今短短几个世纪前欧洲使用的
轮刑、烹刑或开膛破肚则温和得多。《汉穆拉比法典》里约有30次提及
死刑,非死刑类的身体惩罚包括割舌、剜眼、削胸和鞭笞。溺死之刑用
于通奸犯、与儿媳乱伦者,以及在酒馆里以水掺酒欺骗顾客的人。木桩
穿刺刑是对强迫他人堕胎的女性的惩罚。
汉穆拉比声称自己是该法典的作者,法典的条款是国家权力的世俗
体现。国家对越轨行为的反应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复仇:以死偿死。复仇
的概念对大多数刑法体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该法典也引入
了“具有表现力的”“刑同其害”的惩罚原则,对罪犯的部分身体实施体
罚,通常是断肢或某种形式的致残。例如,如果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
西,他将要支付罚金或被砍掉一只手;若再次犯同样的罪行,则会被砍
掉另一只手。如果一个男人亲吻一个已婚女人,他将被割掉下唇。类似
地,猥亵案的罪犯会被砍掉手指,强奸犯会被阉割,而那些诽谤他人的
人会被割舌。
《汉穆拉比法典》或许也是第一部涉及经济犯罪的法典。法典中提
到了对窃贼的惩罚,但也适用于“酒馆招待”——通常是女性——的诈骗
行为。她们不“接受人们用谷物按重量支付酒资,而是要收钱,且酒的
价格低于谷物的价值”,从而触犯了法律。[20]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女
人“应被定罪且扔进水里”,即被溺死。地位、罪行与惩罚
在汉穆拉比时期的巴比伦,社会等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因此,他的
法典成了富人的法律,明确规定侵害者和受害者的社会身份将决定适用
何种惩罚。对罪行的惩罚取决于受害人和罪犯分别属于三个等级中的哪
一个。例如:“如果贵族打断了另一名贵族的骨头,侵害者将被打断骨
头。如果贵族伤了一个平民的眼睛或打断了平民的骨头,他要为此赔付
一米那[21]
的银子。如果贵族伤了另一名贵族的奴隶的眼睛或打断了奴
隶的骨头,则要赔付该奴隶身价的一半。”这种分级惩罚体系取决于犯
罪行为的严重性和罪犯的社会身份。普通女性可以去酒铺,但如果女祭
司走进酒铺则会被判火刑。如果酒铺的女老板在分量上做手脚,会被投
入河中;但如果她允许强盗利用她的店铺接头,她会被处以死刑。
依照受害人和侵害人的地位决定惩罚的尺度,并非巴比伦独有。印
度的《摩奴法典》也是根据当事人的种姓等级来惩罚犯罪行为。高等级
的婆罗门通常只会被判处罚金或不受任何惩罚。他们即便杀了人,也至
多被判放逐。另一个极端是低等级种姓的首陀罗,他们即便犯了最轻微
的罪行也会受到体罚。根据《摩奴法典》:“首陀罗若扬起手或棍子,就要砍掉他的手;如果愤怒时用脚踢人,就要砍掉他的脚。”谋杀婆罗
门是死罪,低等级种姓的人攻击或诽谤高等级种姓的人则会受到“刑同
其害”的惩罚。例如,如果一个首陀罗伤害了一名婆罗门,该首陀罗在
攻击中使用的肢体就要被砍掉,向高等级种姓的人吐口水则会被割掉嘴
唇。类似地,如果他把尿撒在了高等级种姓的人身上,会被割掉阴
茎,“如果他冲高等级种姓的人放屁,就会被割掉肛
门”(Ⅷ:279~280,282~283)。他有诽谤行为,会被割掉舌头,对使用冒
犯的语言提及高等级种姓人的名字和种姓的行为,惩罚是把“十根手指
长的铁钉”和“烧红的钩子”塞进他的嘴里(Ⅷ:270~272)。在唐朝(618—907),中国人也依等级量刑。地位高的罪犯可能会
受到较轻的惩罚,或者完全免于惩罚;而犯了罪的仆人和家奴会受到较
常规惩罚重一等的惩罚,至于奴隶则要加重两等。比方说,如果一个奴
隶攻击平民,使其四肢或眼睛受伤,该奴隶会被处死;相反,如果主人
(无缘无故地)杀死自己的奴隶,至多会被判一年劳役。我们从不同的
资料中发现,在墨西哥早期的阿兹特克文明中,阿兹特克人同样依等级
量刑,但具体的方式略有不同。比如,若案件涉及公开酗酒、行为有失
身份的情况时,对贵族的惩罚比对平民的更严厉,但在通奸案中,贵族
受的惩罚较轻。[22]
直到20世纪,很多非洲国家仍沿用习俗规范进行判决和惩处。比如
在尼日利亚,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决定着他要受的处罚。首领或富人不会
因杀人被处死,他们可以将奴隶作为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或让奴隶代
替自己被处死。同样的案件,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支付罚金,地位较低的
人则要被判奴役。[23]
20世纪的菲律宾伊富高人依旧认可贫富有别;社会地位不同,相应
的罚金也不同,这与《汉穆拉比法典》的规定大同小异。他们明文规
定,若犯杀人罪(无须血债血偿时),富有的罪犯要准备“丰盛的宴会
和各种物品分发给死者的继承人”,除非受害者是下等人。若受害者来
自中等或更低种姓的阶层,赔偿会少得多。然而,如果行凶者属于较低
的两个种姓,无力以“物质代偿”的方式支付罚金,则不仅他的余生要背
负这笔债务,甚至还要父债子偿。[24]摩西律法和近东地区的传统
《汉穆拉比法典》对希伯来律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
上,希伯来律法中的大量词汇均出自苏美尔和巴比伦的法律传统。例
如,现代正统犹太教徒使用苏美尔词语表述离婚,这表明希伯来词语
keritut(分离或中断)有可能源于古苏美尔人的做法:丈夫“割断妻子衣
袍的一角以象征割断婚姻纽带”。[25]
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当正统犹太
教徒在犹太教堂里诵读《摩西五经》时,仍然会用祈祷披肩的边缘触碰
卷轴上的相应地方。他们做得如此自然,并未意识到其实自己正重复着
一个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传统,即要求人们用外衣的绲边拂拭陶碑以表
示对法条的遵从。[26]
无论如何,包含了《十诫》的《圣经》前五卷,也就是希腊人所谓的《旧约》首五卷、犹太人所谓的《摩西五经》,为
西方世界大部分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圣经》中描述的传统家庭类似于一个以父亲为首的、拥有生死裁
量权的大家族。在古希伯来人的村落里,权力掌握在父辈们手中,他们
也是整个社群的首领,这体现了男性主导的司法体系。家庭中往往包括
若干对有生育能力的成年人和他们的子女,人数足以自我保护并自给自
足。当家庭中的一名子嗣或某个家庭成员被另一名家庭成员伤害时,将
由父亲决定赔偿的数额,而这个数额通常取决于在儿子受伤休养期
间“损失的工作量”(《出埃及记》,21︰18~19)。如果坚持要伤害行
凶者,则会令家庭损失两个劳动力,反倒事与愿违。如果受伤的是女
性,则赔偿取决于袭击行为对其日后生育能力造成的影响。在杀人案
中,如果凶手与受害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即为手足相残;若凶手来自另
一个家庭,则被视为谋杀。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将遵循对等原则进行处
罚,一命偿一命。村民会议将决定是判凶手本人死刑,还是让其家中的
另一名成员顶替。另一方面,村名会议也有可能允许凶手的家庭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赔偿。是否适用死刑判决,需要从整个村庄的最大利益着
眼。如果会议认为不诉诸以命偿命的方式更有利于村庄,则可以适用赔
偿。[27]
随后,凶手要向受害者家属献出土地和子嗣。与希伯来人相
似,非洲的一些村落也用赔偿替代死刑,赔偿给受害者家庭的通常是牲
口、与受害者身体条件相仿的人,或可以为受害者的家庭生育子女的女
性。
虽然摩西律法并未跻身世上最伟大的法律体系之一,但它的《十
诫》或许是史上最著名的行为禁令;所不同的是,《十诫》没有包含对
每一种罪行的具体惩罚,因此不应被误认为是法典。希伯来律法讲求刑
同其害(受害者受到怎样的伤害就怎样惩罚凶手)。“以眼还眼,以命
偿命”这句谚语最好地诠释了他们的罪与罚。这种严格字面意义上的罪
与罚在《出埃及记》(21:23)里是这样写的:“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
打。”直到后《圣经》时代,评论家才开始用比喻手法诠释这些词,给
惩罚设置了诸如“至多一只眼”或“至多一颗牙”的限制。彼时的着眼点已
明显从身体伤害转到了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上。
巴比伦律法和犹太律法有几个主要分歧。在古代以色列,涉及财产
的罪行从不会被判死刑,而是适用罚金。由于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人是根据上帝的样子造出来的,因此摩西法典在很多方面比早前近东地
区的律法宽容得多,它既尊重身体,也极力避免部落流血。相反,在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杀人案中,受害者可以接受经济赔偿;而根据犹太律
法,已定罪的凶手则会被处决。根据希伯来《圣经》,夺去人类的生
命,即杀人行为,只有在自卫、战争和适用死刑时才被允许。古代希伯
来人确定了36种当判死刑的罪行,包括杀人、某些性犯罪、偶像崇拜、亵渎神明、不守安息日和行巫术;上述种种日后都在西欧产生了影响,令成千上万名女巫在5至17世纪命丧黄泉。
非死刑罪行通过各种非致死的手段进行惩罚,包括监禁、放逐、罚款和刑同其害的惩罚等。对于非故意杀人或过失杀人,罪犯有可能被判
放逐到六个避难城市中的一个,但绝不会被放逐到非犹太人的土地上,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被迫崇拜异教神明。同样,在避难城市
中,罪犯会受到保护,以免遭受害者亲属的私刑。正如我们前面提到
的,刑同其害的惩罚会让罪犯承受与受害者相同的伤害。放逐一直持续
到该城的大祭司去世。被判放逐的罪犯自然希望刚刚到达流放地就有年
长的祭司去世,因为倘若大祭司年富力强,这放逐恐怕就成了终身监禁
了。在罪犯被迫住在避难城市期间,当地的大祭司家庭会为他们提供衣
物、住宿和食物。
《圣经》中提及了一系列处决方式,包括火刑、石刑和斩首,其中
最常见的是投石击毙,即石刑。这种刑罚的参与者包括整个社群成员,特别适用于被认为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大威胁的那些罪犯。行刑时,提起
诉讼的证人要最先投掷石块,其目的在于杜绝不实控告。石刑是死刑惩
罚中最古老的一种。两千多年来,这种惩罚手段已经在许多国家使用。
最早规定该刑罚的是摩西律法,但由于伊斯兰国家在当代也偶尔使用,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或许与后者的联系更密切。最近的两次石刑分
别于2007年和2010年发生在伊拉克库尔德雅兹迪(Kurdish Yazidi)社区
和阿富汗北部地区;在后一起事件中,一对年轻夫妇因谋划私奔而被石
刑处死。石刑往往遵循特定的程序,受刑的男性在行刑前要被埋及腰
部,女性则要被埋及颈部。如今的宗教法庭规定行刑用的石块要足够
小,一方面要避免受刑人过早地一命呜呼,另一方面也要足以造成确实
的肢体损伤。一次石刑短则10分钟,长则20分钟。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83%的巴基斯坦人认为通奸
犯应用该刑处死。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称,就在2008
年,有1000多人目睹了索马里一名年仅13岁的女孩被石刑处死的过
程。[28]
斩首作为最迅速也最人道的处决方式,适用于那些故意杀人和集体
叛教的罪犯。在21世纪的人看来,斩首等古老的行刑方式似乎已被抛诸脑后。然而,在过去10年中,伊斯兰极端分子采用这种方式惩罚某些西
方人。有人认为,这种方式起源于古代中东地区,曾一度被所有主要宗
教采用。公元627年,先知穆罕默德下令用斩首的方式处死600名麦地那
附近的犹太部落成员,理由是他认为他们犯了通敌叛国罪。巧合的是,他最宠爱的孙子侯赛因·宾·阿里(Hussein bin Ali)于680年在卡尔巴拉
(Karbala)被斩首,且首级被盛在银盘中,经由大马士革送往开罗。斩
首在今日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仍是官方惩罚手段。在沙特阿拉伯,仅
2003年就有52名男子和1名女性被斩首,他们所犯的罪行从杀人、抢劫
到同性恋、贩毒不一而足。如今,罪犯在被带往公共广场之前往往先会
被注射镇静剂,蒙上眼罩,戴上脚镣,双手铐在背后,然后被斩首。虽
然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反复呼吁,但沙特人严守伊斯兰律法,对一系列
罪行实施死刑。实际上,大部分沙特公民被处决的可能性很小,而大多
数贫穷的外来劳工往往更有可能成为刀下鬼。但1977年,该国开国国王
的曾孙女与其情人却双双被处死,她本人遭枪决,其情人则被斩
首。[29]
大多数神职人员之所以指责恐怖分子将斩首作为惩罚手段,不
是因为这种举动是非伊斯兰式的,而是因为它被滥用了。
尽管如此,若是将斩首视为伊斯兰文明所特有的行为就大错特错
了,因为斩首在很多文明中都被用作绞刑、钉十字架或开膛破肚的人道
替代手段。斩首是否真的人道,取决于刽子手的冷静程度。1587年,苏
格兰的玛丽女王被处死时,刽子手可能是喝醉了,砍了三刀才让尸首分
家。英国人在1076年通过了砍头的法律,开始对高等级罪犯适用斩刑。
500年后,对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叛国罪惩处被减刑
为简单斩首,令他免受先被吊个“半死”,然后活生生遭肢解,即“割掉
私处、开膛破肚、灼烧内脏,四肢分挂在四个城门上,首级悬在伦敦桥
上”的酷刑。
在《圣经》时代,火刑是对九种乱伦行为和一种通奸行为的惩罚。
火刑,或许是因为象征着通过刑罚让罪人得到净化,因而更多地被用于
道德犯罪。有了针对部族相残的禁令后,对体罚的设计少了些血腥,但残酷程度丝毫不减。到了后《圣经》时代,那些因乱伦和通奸被定罪的
人会被判处缢毙。行刑时,两名见证人各执绳子的一端,绳子用光滑材
料包裹,以免划伤受刑者的脖子。当死刑犯张嘴奋力呼吸时,熔化的铅
水就会被灌进他的喉咙,烧灼其内脏。
古代以色列人使用的更痛苦的体罚之一是棒刑,该刑罚适用于168
种罪行,包括7种乱伦行为、8种违背饮食教规行为、3种祭司违反婚姻
法的行为、与私生子或基甸人的后代通婚、与经期女性发生性行为等。
在后《圣经》时代,鞭刑和棒刑的上限是40次;渐渐地,人们意识到应
该根据罪犯的身体条件适度行刑,也就是说,量刑以法庭估计的罪犯的
承受度为限。以40次为上限的做法体现了更人道的精神。埃及
埃及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大约同时兴起,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很大
程度上要归功于邻近的广阔沙漠为其阻挡了潜在的入侵者。埃及几千年
的历史比苏美尔王朝延续得更久,主要是因为后者位于开阔的平原上,便利的地理条件成了持续不断的战争的温床。相反,埃及的地理位置相
对孤立,在这里居住的种族也更单一,因此,与古代近东地区的众多文
明自相残杀不同,埃及人学会了在尼罗河沿岸共存,共同抵御每年一次
的洪水,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埃及文明能持续27个世纪。[30]
我们关于埃及早期罪与罚的认知,用一名埃及学家的话说,乃是来
自“法庭文件、市民契约、私人著作、行为举止、虚构故事和一些王室
法令的随机组合”。[31]
从这些资料里可以看出,埃及的罪行包罗万象,从末经许可强借驴子,到盗窃、暴力抢劫、诈骗、逃税、谋杀和罪大恶
极的弑君罪等听上去更现代的罪行,不胜枚举。按照现代西方的标准,埃及人对有罪者的惩罚既迅速又严酷。那些被定罪的人,轻则被判苦
役、鞭笞或各种肉刑;重则要受桩刑,被“置于木桩顶端”缓慢、痛苦地
死去。最高法律实施者代表着国家权力,因此古埃及法老是法律的最终
制定者,有权引入新的法律和惩罚手段。
根据一些保存最完好的关于第十九王朝塞提一世(Nineteenth
Dynasty of Seti I)时期的资料,对偷盗神明供奉者的惩罚包括“杖两
百,割五刀”。但痛苦的杖刑、割刑、断肢刑和死刑,既是为了让受刑
者蒙受痛苦与屈辱,也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重申其作为警告他人的权
力”。[32]
自第十八王朝起,体罚和(或)经济惩罚成为常态,死刑也在
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惩罚手段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彼时,埃及几乎
不使用货币,这意味着赔偿主要限于“肉刑和劳役”。正是在这一时期,“欠税者马利成了(或许是)第一个因被判鞭刑而名留史册的埃及
人”,他因“不实诉讼”挨了一百鞭。[33]
到第十八王朝末期(公元前13世纪),对罪犯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观
点已成为规范。严刑峻法被用于惩治官员腐败。如果一个人因阻止尼罗
河上的自由通行而被判有罪,他将被割掉鼻子,流放到西奈沙漠的一个
社区。各种新残害被用来标记罪犯(从而确定他们的罪行)。割耳和割
鼻最为常见,适用于苦行犯,因为面部的损毁并不会妨碍劳动。有学者
认为,当时的社会中可能不乏畸形人,他们的身体要么毁于疾病或糟糕
的医疗技术,要么在可怕的意外事故中受伤,因此面部损毁和其他残害
带给公众的惊惧可能并没有如今那么强烈。割鼻和割耳虽然痛苦,却很
少导致死亡或并发症。由于这两个器官主要由软骨构成,基本不参与血
液循环,因此出血的风险极低。受刑者或许会出现呼吸或听力问题,但
这对身体的损害远小于削手和断肢。[34]
死刑主要适用于背叛国家(国王以及他所代表的神圣秩序)的罪
行,相比其他古代社会,埃及的死刑判决似乎相对较少。人类历史上现
存最早的书面死刑判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埃及,当时一名罪犯
因施魔法被判死刑,且被要求自裁。处决往往是公开执行,虽然场面不
如后来古罗马斗兽场中的那般精彩,却是国家对潜在违法者的警告。当
涉及叛国、叛乱和通奸罪时,这种意味尤为明显,罪犯有时会被处以火
刑。在其他情况下,平民处决的首选方式是被钉在木桩上,而对杀人犯
则适用斩首。[35]
与大部分古人一样,埃及人将弑亲视作最严重的罪
行,并给予更严酷的惩罚。弑亲者会赤身裸体滚过荆棘,然后葬身火
海;若母亲杀了孩子,则会被迫将孩子的尸体绕在脖子上,直到其腐
烂。
官方使用的三种逼供方法包括笞打脊背和四肢、威胁放逐到努比亚
(Nubia,苏丹),或斩断部分肢体。最常见的体罚形式似乎是鞭笞,残害则适用于更严重的罪行。杀父母者要被碾过荆棘然后活活烧死。犯通奸罪的男性会被处以1000下鞭刑,女性会被割掉鼻子。强奸犯会被阉
割,叛徒则会被割掉舌头。
从理论上说,同样的法律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即使是最富有的贵
族也不能逍遥法外。任何等级的人如果犯叛国罪这样的罪行都会被严
惩。埃及的文献中充斥着抢劫、偷窃、入室盗窃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的记
录,包括团伙盗墓并抢劫,其年代可以追溯到拉美西斯九世(Ramses
IX)统治时期。
埃及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肉体和灵魂,并将肉体的死亡视作生命的中
断,而非终止。此外,他们相信随着死亡的到来,死者将面对奥西里斯
(Osiris)和地狱四十二判官的审判。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死后不得安
葬。正因如此,处以火刑会对亡者无尽的阴间生活带来极大伤害,因为
没了躯体,亡灵就无法通过审判。一个人的来世或受折磨或交好运,影
响来世的一系列律法在埃及的《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中均有记
载。古代中国
3000多年前,《易经》以非常含蓄的方式提到了一种名叫“何校”的
惩罚:“何校灭耳,凶。”校即枷,是一种笨重的木质项圈,约3~4英尺
见方,中间开有一孔供头伸出。枷被固定在佩戴者的脖子上,其宽度使
得佩戴者的手无法触及面部。视情况而定,罪犯会被判戴枷1至2个月不
等。通常而言,这种惩罚含有羞辱的意味,戴枷者要被迫坐在其实施犯
罪行为的地方。到了夜晚,他会被一个官员带回牢房,如果运气好,他
可能会被允许摘下木枷,直到第二天。此外,倘若没有人为他提供食
物,他还不得不靠乞讨为生。
帝制时期的中国刑罚制度源远流长。古中国的刑罚与西方和近东地
区建立的制度和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或
天然、或人为的与世隔绝状态。孤立保障了中国司法体系得以独立发
展,不受或多或少源自美索不达米亚法律的中东法典和欧洲法典的影
响。
到公元前22世纪,中国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在很多情况下,人
类早期社会为惩治恶行而发展出的刑罚手段大同小异;而在中国,即便
是早期,惩罚手段的划分也相当清晰,从罚款、黥到笞、劓、刖、宫等
肉刑不一而足。此外,它有一个突出特点:衣着服饰也是惩罚的一部
分。受黥刑的罪犯只能戴头巾,不能戴帽子,因为后者会遮挡其面部。
那些被判刖刑的罪犯可以穿麻衣,但不能穿丝绸服饰或草鞋。受宫刑的
人不得穿长袍,只能穿及膝短袍,(截短的袍子)表示他遭受了阉割之
刑。类似地,被判斩首的人只能穿无领短衣。但这些惩罚手段显然只适
用于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因为律法中还规定了各种宽大条款。与后来
的不少社会一样,只要有可能,流放往往成为代替刑罚的手段。杖笞是宋朝(960—1279年)常见的刑罚。根据法律,行刑用竹
杖,上限为40下。行刑规范要求罪犯趴在地上,解开臀部周围的衣物,以臀部接受杖打。如果是女犯,则可以跪在地上,只脱去外套,以背部
或腿部受刑。刑罚的严酷程度取决于笞打的力度而非次数,贿赂行刑者
以求手下留情的现象自然免不了。还有一种肉刑是用1尺长的皮条(2~3
英寸宽)抽打脸部。行刑时,罪犯跪在地上,行刑官一只手抓住罪犯的
头发,一只手用皮条抽打。抽打次数被限定在20到30下,但这并不能避
免罪犯的嘴唇时有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情形。[36]
虽然超出常人想象力
的非法酷刑的确存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刑罚限于流放、监禁和斩
首。古希腊
古希腊是数百个独立和半独立城邦的集合体,而非一个统一的国
家。在这些城邦中,雅典声名远播,几乎成了希腊在古代的代名词。形
成于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法典在很多方面皆异于早前的近东法典和摩西
律法。与万能的汉穆拉比王颁布的法律和由摩西律法所代表的上帝之法
不同,雅典律法乃是基于民众的意见。大体而言,希腊人吸收借鉴了美
索不达米亚律法和东方法律的思想,并塑之以西方特色。不过,与古代
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并未直接接触东方文化。这两种文明之间有着天
壤之别。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是绝对的统治者;而希腊人,至少是雅
典人,却对公民权利有着基本的尊重。但无论如何,希腊法律毫无疑问
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伯来律法的间接影响。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古代雅典人非常害怕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或在
大街上或公共场所被抢劫财物。[37]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普罗塔哥
拉和其他雅典人很早就提出了贫穷与由贫富差异造成的罪犯之间的因果
联系。尽管如此,贫穷并未因此成为偷盗、抢劫等罪行免遭惩罚的理
由。被抓的抢劫犯与入室窃贼若不能在审讯中提供任何辩护,将被依法
处决。处决常常含有某种公开羞辱的意味,罪犯会被钉在木板上慢慢等
死,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勒死。在罪犯被处以罚款的情况下,也可以同
时附加某些羞辱刑,比如束缚在枷具上五日等。
在荷马时代(Homeric Age,前8世纪),古希腊出现了刑法制度的
第一次重大飞跃,正义的齿轮开始绕着受害者与罪犯之间的非正规程序
旋转。在通奸、诱奸和强奸案中,应由被戴绿帽子的丈夫或其最亲密的
亲属(当受害人是自由女性时)来主张正义;若受害人是奴隶,则由其
主人提出诉讼。偷牛、抢劫和海盗等罪行不仅常见,而且威胁到整个社
会,因此应由社群提出集体诉讼。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凶杀案,凶手会被放逐。如果行凶者和被害人没有亲属关系,则行凶者通常会尝试逃亡
或支付赔偿,以免死于受害者家人的怒火之下。
古希腊的第一部成文法当归于政治家德拉古。公元前7世纪,他受
命编写一部新的法典,以遏制氏族仇恨、控制民众动乱。据说,他对几
乎所有违法行为都残酷无情地施用死刑,“严酷的”(draconian)一词便
由此而来。对德拉古的法典,我们基本上只能通过后世希腊历史学家的
著作来了解一二。据普鲁塔克记载:“就连那些偷沙拉或水果的人也会
受到与亵渎神明或谋杀犯相同的惩罚……德拉古的律法不是用墨水,而
是用鲜血写成的。”[38]
不过,我们对希腊历史早期的罪与罚的实际了解
仅限于那些涉及凶杀的案件。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司法革新是建立了专门
审判杀人案、纵火案和其他严重罪行的雅典最高法庭(Court of
Areopagus)。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受害人在临死前拥有宽恕凶手的权
力,可使凶手免于惩罚。稍晚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证实了这
一点,他写道:“如果受害者本人在死前为凶手开脱了罪责,则其他家
庭成员不得继续控告他,除非凶手已被定罪;驱逐、流放和死亡由法律
决定,罪犯一旦被赦免,就不再受其他任何控诉。”[39]
为了避免无止境的仇杀,德拉古法典给了凶手三个选择。他们可以
认罪并被立即放逐;可以服从审判,在判决确定前遵守规定并依旧享有
自由,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得出现在祭祀和公共场所;他们还可以不选前
两条路,不过倘若如此,罪犯有可能因出现在公共场所或圣地而被雅典
人当场杀死或逮捕(这是市民拘捕的雏形)。在德拉古的法典中,我们
可以看出对正当杀人与不正当杀人的区分,二者适用不同的处罚。只有
在预谋杀人或主动杀人案中,城邦才有权做出死刑判决。同时,法律允
许受害者家属接受赔偿,以代替城邦处罚。
与其他类型的犯罪不同,杀人案的诉讼期不受时间限制,受害者家
属对侵害者的合法报复也不受时间限制。如果受害者家属不采取行动,就会让家庭蒙羞。此外,雅典人担心有罪之人会因未被及时发现而逃脱审判。这一点对现代司法影响深远,在美国,谋杀罪仍是少数没有诉讼
时效的罪行之一。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罪与罚的认知仅限
于杀人罪。我们知道,非故意杀人的罪犯会被处以刑期不定的流放,只
有当受害者亲属同意时,流放方能结束。当时的一段文字记录了一名被
判终身流放者的话,他哀叹道:“若被判死刑,我所做的恶将会令子孙
蒙羞;若被流放,我将无家可归,在异乡乞讨终老。”[40]
被流放的罪犯
在流放期间会受到保护,免遭暴力或威胁,如果他受到伤害,行凶者将
被惩罚。然而,一旦他提前从流放地返回,他所受的保护也将不复存
在,很容易成为复仇者的目标。
故意杀人、行凶、纵火、投毒案会在雅典最高法庭审理(非故意杀
人行为不受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决工具从沉重的木头变成了
剑。用于行刑的木头究竟是何模样,目前尚存争论,但有可能类似棍
棒。考古学证据显示,还有一种处决方式规定,要把罪犯的脖子、手腕
和脚踝分别用五根铁箍固定在一块直立的木板上,然后或者任由他忍饥
挨饿慢慢死去,或者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收紧绕在罪犯脖子上的铁箍将
其勒死。
希腊人提到“穿石衣”的做法,我们可以推断,石刑在古希腊是一种
正式的处决手段。早期希腊的刑罚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允许适用赔偿方
式,对杀人犯和叛徒则往往适用投石处死或毒芹处死。英雄时代的希腊
人也采用坠落处死的方式,即将罪犯扔下绝壁。这种刑罚往往也包括把
罪犯猛地从高石台上扔下或推进深坑,由于坑里布满专门用来刺穿身体
的尖刺和钩子,因此可以确保其死亡。到公元前5世纪,毒芹取代了深
坑。与此同时,绞刑、钉十字架和用棍棒殴打致死的方式也投入使用。
与斩首、断头台、现代毒气室、电椅和注射死刑一样,毒芹的使用标志
着死刑人道化的早期尝试。在众多使用这种从种子和茎叶中提取的黏稠
毒剂的案例中,最著名的当属对70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处决。公元前
399年,他因败坏雅典青年、拒绝承认城邦神灵的罪名被判死刑。死于
毒芹之下当然不舒服,死亡常常伴随着痉挛和抽搐,但这种方式仍被视作不流血的文明手段。
偷窃某些蔬菜和水果、亵渎圣物、游手好闲和杀人都是死罪。事实
上,德拉古法典或许并不比传统习惯法更残酷,但因其未对法律体系做
出任何彻底变革,因而招致雅典民众的不满,留下了恶名。德拉古法典
代表了从前文字时代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
人们遵守某种固定不变的法律程序,并给出了各种罪行的预定惩罚。为
了公示于众,法典中关于宗教的条款被刻在木头柱子上,其他条款则被
刻于铜柱之上。
到了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对杀人罪的态度变得令人
费解。与早期其他社会的做法一样,受害者家庭有责任寻求惩罚或复
仇。然而,这绝非单纯的“以眼还眼”。除了复仇之外,赎罪也必不可
少,也就是说要让城邦免受杀人罪行的污染。人们认为,凶手的手是肮
脏的——被罪行玷污了——且会污染所有和他接触的人以及发生罪行的
整个城邦。为了净化城邦,要由受害者家属决定,或者对凶手实施复
仇,或者达成某种和解,让受害者家庭能最终宽恕凶手。[41]
雅典人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任何不忠诚或背叛的行为都会被视作
最严重的罪过,将被城邦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但对很多罪犯而言,最
糟糕的莫过于死后不能埋在雅典。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特米斯托
克利因叛国罪被处决后,他的朋友将其尸骨偷偷带回雅典埋葬,这便是
极好的例证。抢劫神庙、施魔法或破坏神像的行为,其惩罚几乎可以与
叛国罪等同。与早前(及后来)的文明相比,当涉及道德犯罪时,希腊
人的态度明显温和得多。在大多数时候,而罪犯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罚也
不过是被拔掉体毛或肛门里被插进一根小萝卜。[42]
但若涉及通奸且被
当场抓获,愤怒的丈夫有权杀死通奸者。这条规定出自德拉古法
典:“如果一名男性杀死了与他的妻子通奸的人……他不会因为该行为
被判杀人罪而遭流放。”当然,他也可以接受金钱补偿,放弃个人报
复。造假币的古老手艺
古代和现代的犯罪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大多数古老的罪行以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摇身一变进入了现代法规。以杀人、抢劫和盗窃为例,这
三种行为很早就被认定为罪行或恶行,尽管具体定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有
所变化。这一点在经济案件中犹然。随着生活日益繁复,且涉及了各种
法律条文,人们有必要通过某种形式的账目来记录一些基本事项,诸如
仓库里有什么货物、市民是否向公共基金缴了应缴的款项。例如,在美
索不达米亚,每个人都要向神明提供供奉。但出于人类的本性,很多人
会设法逃避(就像今天的人逃税那样),声称他们已经“付过了”或捐献
过了。用楔形文字或埃及象形文字记录的账目不仅使文明社会得以采用
更高级的统治形式,也确保了特定责任得到履行。
早在公元前3000年,继书写和有组织耕作之后,货币作为另一种文
明迹象也出现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尽管如此,早期的货币乃是金
银,而非铸币,因此其价值取决于交易金属的重量。别忘了,人类的本
性中有着对犯罪行为不同寻常的偏好。很多证据表明,人们自古便试图
伪造金属货币,后来则发展成伪造皇家铸造的硬币。受德拉古的影响,公元前7世纪的梭伦成了法治的热情支持者,他坚持认为,只有严惩偷
窃或挪用公款等罪行,法治才能向前推进。
相比之下,《圣经》不太重视涉及财物的犯罪,不像古代世界其他
地方的法典那样对该类犯罪适用体罚或死刑,而是判处支付罚金和赔
偿。
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伪造者的技艺已相当精湛,掌握了用来浇铸
金属的陶土磨具的制作工艺。历史资料显示,伪造者会被处以最严酷的
刑罚。君士坦丁大帝曾将这些人活活烧死。从硬币上切削、熔化稀有金属的人会被“切削或割掉”耳朵。其余相关罪犯会被剥夺公民权。随着帝
国的壮大,伪造者若是不被阉割或扔进狮笼,至少也会被割掉鼻子。尽
管如此,当帝国日薄西山之际,伪造之风却在古罗马贵族间悄然兴起。
严惩伪造者的做法也延伸到其他社会。随着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的
不断扩张,伪造者会被处以剁手之刑。在7世纪的中国,对伪造者的惩
罚是黥面,之后发展到死刑。到了14世纪,中国甚至在钱票上印着“伪
造者处死”的警告。[43]奴役和监禁
奴隶制度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奴隶的社
会不在少数,包括希腊人、朝鲜人、印度人、美洲原住民、古罗马人、维京人、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建立的社会。大多数观点认
为,奴隶制“在所有古代文明社会中都被视作自然和合理的社会制
度”。[44]
奴隶的生命都比较短暂,埃及人用奴隶为皇室成员陪葬。事实
上,在不少社会中,人们购买奴隶的主要目的正是作为牺牲。不过,在
很多情况下,奴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强制劳动,也是一种惩罚制度。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提到,公元前11世纪,埃塞俄比亚国王萨巴
科斯(Sabacos)——此人后来也成了埃及的统治者——用“想必也伴随
着监禁”的强制劳动取代了死刑。与19世纪基于人种的奴隶制度不同,在当时,人种并不能决定某人是否会受奴役。在古代刑罚实践中,人们
更常用罚款或放逐作为惩罚手段,除非需要大量劳动力去完成某个超出
早期社会能力的工程。在足够先进的技术出现之前,奴役劳工是获取大
量劳动力仅有的几种方式之一。因此,只有当需要调动劳动力开采稀有
金属,修建金字塔、道路和纪念碑时,强制劳动才会成为社会的惩罚手
段。[45]
从我们现有的少量证据中可以看出,蓄奴出现后,将奴役作为惩罚
手段便失去了明显的意义。不过,这个变化在古代近东地区和古希腊并
不突出。在埃及,因罪沦为奴隶的主要原因是欠了国家债务。在古代朝
鲜,因叛国、抢劫和屠杀珍贵家畜而被定罪的人,其家属将沦为奴隶。
在中国汉朝以前,死刑犯的家属会成为奴隶。自此,因罪成奴不仅是主
要的,也是唯一被认可的奴隶来源。因此,中国的奴隶制与惩罚制度相
伴相行。所有犯了罪并被判奴役的人通常都会被刺上某种刺青或毁容,以区别于自由民。这种罪犯标记乃是人口买卖的最重要的基础。此外,与近东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刑事制度强调家族纽带和责任,一人犯罪,其家庭成员和旁系亲属往往都会受牵连。[46]
在不使用奴役作为惩罚手段的早期社会里,为了强迫债务人还债或
控制那些等待审判和惩罚的罪犯,必然要使用某种形式的监禁措施。古
代监狱与现代监狱的区别在于,早期的监狱不是专门建造的。大部分关
于古代刑罚的历史记录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与现代刑事体系的其他诸
多方面一样,监狱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当然,究竟早到何时,目前并没
有确凿的证据,但坟墓、处决室和在战争中用于关押奴隶的地方已存在
了数千年。关于这方面的最早期信息的确相当匮乏,但在埃及象形文字
记录、希腊神话和《创世记》中绝非一笔带过。将某人关押起来然后扔
掉钥匙的做法自古有之。
纵观历史,早期社会追求的是迅速、确定的惩罚,无论断肢、罚
款、流放或死刑皆是如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监禁亦属于这一类惩
罚。现有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建筑奇
阿普斯(Cheops,希腊人对胡夫的称呼)大金字塔(约前2650年建成)
内有个地下深坑,据说是“迷失者的牢房”。与此类似,几百年后,埃及
人把建于第六王朝泰蒂(Teti,约前2345—前2333年)时期的萨卡拉
(Saqqara)金字塔称作“金字监牢”。坐落于它东边的另一座金字塔,其
阿拉伯语名称的意思是“卓瑟的监狱”。在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和其他地方保存着大量关于在这些古迹中实施监禁的图画。1799年被发
现的罗塞达碑上甚至多次提到了监狱。最古老的埃及墓地可以追溯到
5000多年前(位于尼罗河对面的孟斐斯遗址),而监狱的符号可追溯到
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房子”和“黑暗”的结合体。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几
乎一无所知。还有大量猜测认为,金字塔是由监狱罪犯所建。[47]
《创
世记》(39:20~40:5)中提到了监禁,古巴比伦人曾使用bit kili关押欠
债者和轻罪罪犯(前3000—前400年),亚述帝国则使用bit asiri(前746
年—前539年)。《旧约》记载了埃及人、亚述人和古代以色列人对监
禁手段的使用。在尼布甲尼撒时代,耶路撒冷至少有三座监狱,分别是:Beth ha—keli,或称拘禁室;Beth haasourim,字面意思是“锁链
室”;以及Bor——地下室。
监狱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资料中也有记载。《尚书》(或称
《书》)提及夏王芬曾建监狱。[48]
雅典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过不
同的刑罚,其中包括罚款、没收财物、公开羞辱和拆毁罪犯的家
园。[49]
雅典的自由民很少被关入监狱,除非是涉及叛国罪或需要用强
制手段迫使债务人偿还城邦债务的情况。那些面临酷刑或死刑处罚的罪
犯会被囚禁,让他们在受酷刑之前先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雅典,甚
至有一座名为“锁链之地”的建筑,虽然或许修建的初衷并非是要作为监
狱。监禁和奴役常常出现在柏拉图(约前300年)的笔下,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好政府的必备要素。苏格拉底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接受入狱惩
罚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提出,城邦应该有三
座监狱:一座位于市场附近的公共监狱,用于关押普通罪犯;一座位于
夜间议事会(Nocturnal Council)附近的“改造中心”;另一座要在荒郊
野外,并配以彰显惩罚意味的名字。柏拉图建议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
度、罪犯的“本性”和具体的犯罪情形确定监禁期,最长可判终身监禁。
不过,他虽阐述了关于监禁体系的理论,却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这些观点
在当时得到实际应用。[50]
1860年,小说家纳萨尼尔·霍桑参观了位于古罗马的马梅定监狱
(Mamertine Prison)。[51]
公元68年,正是在这里,圣徒保罗被尼禄处
死。这座位于市场里的宏大建筑是专为等待处决的罪犯准备的监牢,起
初叫carcer(监牢),从中世纪起被称为马梅定监狱,“监
禁”(incarcerate)一词由此而来。私人监狱(carcer privatus)在古希腊
和古罗马均偶有使用,主要关押欠债者和等待审判或处决的人。古罗马
的第一部成文法(参见第二章)《十二表法》(Twelve Tables)提到了
被称为ergastalum的强制拘禁所。不过,各种监牢中最令人胆寒的当属
dungeon。该词源自拉丁文dominium,指的是建在绝壁上的城堡或要塞,后来在法语中演化成donjon,之后又变成了那个我们更熟悉的英语
词。随着时间的推移,dungeon成了地牢和黑牢的同义词。小结
在复杂的法律、审判和监狱体系建立之前,早期社会依靠习俗、巫
术和宗教来维护社会秩序,而彼时的习惯法往往比现代成文法更死板。
在国家诞生之前的社会里,律法常常或源出神明或由部落首领确定,通
过判决或立法程序制定法律的方式则要晚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
段,法律都被视作神明直接命令的衍生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完
整法典描述了太阳神(也是正义之神)沙玛什(Shamash)登上宝座并
将法令交给虔诚的苏美尔国王汉穆拉比的故事。[52]
与此类似,几个世
纪之后,当摩西登上西奈山时,耶和华亲手将《十诫》刻在两块石板
上。虽然《十诫》中的某些条文可以从《汉穆拉比法典》中找到踪迹,但在希伯来人的故事之前,《十诫》本身并不存在。有学者认为,最早
的与《十诫》类似的叙述可见于埃及人的《亡灵书》第125章,书中提
及进入公正之地的死亡宣言:“我从未轻慢神明。我从未杀人。我从未
教唆他人行凶。我从未通奸或行不洁之事。我从未偷盗。我从未说
谎。”无独有偶,据说克里特之王米诺斯(Minos)每9年就要登上奥林
匹斯山接受宙斯的法律忠告。
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程序影响了很多同时代的国家,包括埃及、波
斯和印度,但其在上述地区的影响力并不如在西方那么深远,也未
能“扎下根”。[53]
《汉穆拉比法典》继续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的惩罚程
序,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与近东接触之后均受到了它的影响。伊斯兰国家
在征服了如今的伊拉克地区之后也有了法典。早期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
人通过对民众认可的特定法律原则的确认完成了立法。而在相对更孤立
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和埃及文明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关于罪与罚
的理念。
最早的法典几乎完全由惩罚条款构成,着眼于惩罚那些最危险的罪行,比如杀人和人身伤害。由于社会发展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彼时
的惩罚手段不似后来那般多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刑罚只是简单地
以命抵命或其他同态惩罚(以相同的手法和相同的程度进行处罚)。一
些世间最常见的罪行及其惩罚可以追溯到古代,其中包括石刑、绞刑、斩首和钉十字架。由波斯人或古代腓尼基人发明的十字架被亚述、古埃
及、古希腊、印度、迦太基、凯尔特和古罗马等文明古国广泛采用,直
到315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才淡出历史。[54]
不过,日本直到19世纪
仍在使用十字架刑。钉十字架传统上是一种政治或军事惩罚手段,迦太
基人和波斯人用它来处决军事指挥官和高级官员。古罗马人则喜欢用十
字架对付下等人、奴隶和暴力犯。严刑峻法以约束民众的理念强化了依
身份量刑的观念,并影响着随后的几个世纪,给贫穷无助的劳苦大众带
去了最深切的苦痛和折磨。
[1]Jean Guiliane and Jean Zammit,Origins of War:Violence in Prehistory(Oxford,2005),p.231.同
时参见Ian Armit,‘Violence and Society in the Deep Human Past,’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LI(2011),pp.499~517。
[2]Ronald Hutton,Pagan Britain(New Haven,CT,2014).
[3]Karin Sanders,Bodies in the Bog and the Archeological Imagination(Chicago,IL,2009),.4.
[4]Karin Sanders,Bodies in the Bog and the Archeological Imagination(Chicago,IL,2009),.4.
[5]R.S.Rattray,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London,1911),pp.232~233.
[6]R.S.Rattray,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London,1911),p.292。
[7]R.S.Rattray,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London,1911),pp.372~375。
[8]为了避免在行绞刑时造成肢体残缺或出血,通常会使用皮绳或徒手操作。当使用棒刑
时,通常会用象牙或某种杵来打死高等级的受刑者。参见拉特雷的Ashanti Law,p.375.
[9]为了避免在行绞刑时造成肢体残缺或出血,通常会使用皮绳或徒手操作。当使用棒刑
时,通常会用象牙或某种杵来打死高等级的受刑者。参见拉特雷的Ashanti Law,p.376。
[10]Jacques Barzun,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to the
Present(New York,2001),p.762.
[11]Robert H.Lowie,Primitive Society(New York,1920),p.401.
[12]Robert H.Lowie,Primitive Society(New York,1920),p.416。
[13]Karin Bullard,“‘Blood Money’could Free American”,Houston Chronicle,5March2011,p.A14.[14]Lowie,Primitive Society,pp.413~414.
[15]Jo Tuckman,‘Vengeance Allowed to Flourish’,Houston Chronicle,30June2002,p.24A.
[16]Reed Lindsay,‘Bolivia’s Aymara Taking Justice into Own Hands’,Houston
Chronicle,26September2004,p.A30.
[17]1英尺≈0.3米。——编者注
[18]大多数已被后来的伊拉姆征服者带到苏萨,并于1901年被发现,如今保存在巴黎卢浮
宫博物馆。
[19]Marc Van De Mierop,King Hammurabi of Babylon:A Biography(Malden,MA,2005),p.99.
[20]虽然我们知道“玉米”是在美洲被发现的,但在前殖民时代,这个词也被用来指代“谷
物”或当地生长的其他各种主要农作物。
[21]米那:古希腊、古埃及等之重量及货币单位。——编者注
[22]Frances F.Berdan,‘Crime and Control in Aztec Society’,收录于Organised Crimein
Antiquity,ed.Keith Hopwood(Swansea,2009),pp.255~270.
[23]Alan Milner,The Nigerian Penal System(London,1972).
[24]Lowie,Primitive Law,pp.402~403.
[25]‘Divorce’,收录于Encyclopaedia Judaica,2nd edn,vol.v,ed.Fred Skolnick and Michael
Berenbaum(Farmington Hills,MI,2007),p.710;同时参见Ruth3:9。
[26]Israel Drapkin,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Ancient World(Lexington,MA,1989),p.32.
[27]Victor H.Matthews and Don C.Benjamin,Social World of Ancient Israel,1250—
587BCE(Peabody,MA,1993),pp.11~12.
[28]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09,‘Pakistani Public Opinion:Growing Concerns about
Extremism,Continuing Discon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t http:pewglobal.org.
[29]‘Saudis Defensive as Swords Swing,Heads Roll’,Houston Chronicle,25April2000.
[30]Drapkin,Crime and Punishment,p.37.
[31]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
[32]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p.65。
[33]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p.72。
[34]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p.72.[35]Pierre Montet,Everyday Life in Egypt in the Days of Ramses the Great(New
York,1958),p.269.该书作者认为,受刑者只是被绑在柱子上等死,而非被刺死。
[36]The Strange Cases of Magistrate Pao:Chinese Tales of Crime and Detection,trans.Leon
Comber(Rutland,VT,1964).
[37]Nick Fisher,“‘Workshops of Villains’:Was there Much Organised Crime in Classical
Athens?”,收录于Organised Crime in Antiquity,ed.Hopwood,pp.53~96。
[38]Plutarch’s Lives(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vol.I,trans.Arthur Hugh
Clough(New York,1992),p.117.
[39]Demosthenes,转引自Douglas M.MacDowell,Athenian Homicide Law in the Age of the
Orators(Manchester,1999),p.8。
[40]Demosthenes,转引自Douglas M.MacDowell,Athenian Homicide Law in the Age of the
Orators(Manchester,1999),p.113。
[41]Demosthenes,转引自Douglas M.MacDowell,Athenian Homicide Law in the Age of the
Orators(Manchester,1999),p.113.
[42]Herbert A.Johnson,Nancy Travis Wolfe and Mark Jones,History of Criminal Justice,3rd
edn(Cincinnati,OH,2003).
[43]John K.Cooley,Currency Wars:How Forged Money is the New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New York,2008),pp.56~62;本部分的标题取自库利书中的同名章节,p.55。
[44]J.Thorsten Sellin,Slavery and the Penal System(New York,1976),p.1;Orlando
Patterson,Slavery and Social Death: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MA,1982).
[45]M.I.Finley,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New York,1980),pp.67~68.
[46]Patterson,Slavery and Social Death,p.128.
[47]汉茨维尔市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里占地1.86万平方米的刑事审判中心是在20世纪70年代
由监狱服刑人员建造的。
[48]此处作者引用的典籍应为《竹书纪年》,其中有“夏后芬三十六年作圜土”的记载。夏王
芬,一名“槐”。——编者注
[49]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国防军在巴勒斯坦人暴动期间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推平了巴勒
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和其他与恐怖袭击有关联人员的家园。
[50]Norman Johnston,Forms of Constraint:A History of Prison
Architecture(Urbana,IL,2000),pp.5~6.
[51]此地现在已向公众开放,本书作者最近曾造访过。
[52]苏美尔曾是古巴比伦的一部分,位于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南半部,亚述则在北部。
[53]Drapkin,Crime and Punishment,p.31[54]Martin Hengel,Crucifixio(Philadelphia,PA,1978),pp.22~23;Lewis Lyons,The History of
Punishment(London,2003),p.162.第二章 法律传统的兴起
虽然大多数现代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当代四大法律传统上,但在历史
上,至少有16种不同的传统曾繁盛一时。1928年,亨利·威格莫尔
(Henry Wigmore)将这些法律体系分别命名为埃及法系、美索不达米
亚法系、中华法系、印度法系、希伯来法系、希腊法系、罗马法系、海
洋法系、日本法系、伊斯兰法系、凯尔特法系、日耳曼斯拉夫法系、教
会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8年之后,威格莫尔认为,上述法系中
有6个已经完全消失[1]
,5个发生了混合,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法系则基
本保持独立。1936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3年,威格莫尔将中
华法系定义为迄今尚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体系。
除了少数实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国家(古巴、中国、越南、朝
鲜)之外,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基于民法传统、普
通法传统或伊斯兰法律传统。当然,采用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的国家
最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殖民势力将这两种法律传统带到了全球。
由于大大英帝国的统治,普通法传统在加勒比、北美、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非洲部分地区、印度等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最年轻,或许也是使用国家最少的主流
法律传统,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动荡
年代里诞生的社会主义法系极大地借鉴了民法法典和俄国习惯法。由于
缺乏系统构架,(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特别法官拥有大量自由裁判
权。俄国民法典深受早期俄国、德国、法国和瑞士民法典影响。古巴、朝鲜、越南和中国是如今仅有的采用社会主义法系的国家,但其各自在
罪与罚的实践上迥然不同,无法一概而论。
几个世纪以来,上述法律传统或经由征战或通过殖民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随后在新家园里因地制宜地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见第
八章)。普通法传入新大陆时必须依殖民地环境进行调整,以便既能适
用于荒野化外之地,亦能与众多高度发达的本土社会相互交融。类似
地,当英国人在非洲、印度和亚洲建立殖民地时,他们的法律体系也被
迫同那些已经有自身的罪与罚体系的复杂社会法律体系展开竞争。到20
世纪40年代末,大英帝国日薄西山,但普通法影响下的刑法判例在从津
巴布韦、尼日利亚到大洋洲、北美洲的各前殖民地生根发芽。
鞭刑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实施,比大英帝国的统治期更长久,被用
于行乞、传播色情作品、叛国和暴力抢劫等罪行。1965年新加坡独立
后,其法典中保留了肉刑,甚至在当年将适用肉刑的罪行增加到30种。
最近的一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旧法律传统在被移植到全新的环境中后是
如何演化的。用白桦木棍笞打是英国殖民司法体系中沿袭近200年的传
统,此类肉刑曾令英国人臭名远扬,以至于被法国人称为“英国之
恶”。[2]
但在1998年3月,英国议会投票废除了笞刑,同样废除该刑罚的
还有其曾经的殖民地新西兰(1990年)、南非(1996年)和苏格兰
(2000年)。然而,笞刑并没有从这个前帝国的偏远角落里消失。1994
年,侨居新加坡的18岁美国人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因受笞刑在
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指责之声多来自西方世界。起初,费伊被控与
53起涉及破坏公共财产的案件有关,最终坐实两项破坏公共财产案、两
起恶作剧和一项藏匿盗窃财产案,并被判有罪。但最令人权观察家愤怒
的是,他被判4个月监禁、2500美元罚款和6下笞刑(申诉后减为4
下)。新加坡受到西方世界围攻,但坚持立场。1994年5月4日,费伊和
其他9名被判同类刑罚的罪犯一起在监狱的笞打室接受了惩罚。他们被
剥去衣服,手脚用带子绑在一张H形的条凳上,肾脏部位被施以保护。
除了行刑手,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一名医务官。一名记者描述道:“行刑
手铆足了劲儿,使出全身力气,挥舞着13毫米厚的藤条。藤条事先已在
水中浸泡了一整夜,以防开裂。藤条抽打在费伊裸露的臀部,每两次之
间大约间隔半分钟。”[3]
整个过程最多用了10分钟。行刑完毕,行刑手和罪犯相互握手,费伊未借助任何帮助独自回到囚室。
虽然新加坡的司法体系根植于英国普通法,但自独立后形成了自己
的法律传统和哲学烙印。不少观察者注意到,英国人喜欢在学校里实施
体罚,这种做法同样被很多前殖民地国家采用。就很多方面而言,新加
坡人已基本抛弃了英国传统,包括在几年前取消了陪审团制度(他们认
为这种制度容易造成错误)。这个城市国家近80%的居民是华人,虽与
中国有不同之处,但其核心价值体系同样强调儒家道德,比如尊重权
威。东西两种世界观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宁可放过罪人也不错杀无辜
的西方观念突显了个体的重要性。相反,亚洲人的观念体现了另一种道
德原则,即宁可错杀无辜以保护大众福祉,不可放过罪人令社会再受危
害。除了考虑到普通法与儒家道德原则的结合,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里
还居住着大量穆斯林,遵从马来穆斯林习惯法的人超过了其总人口的
16%。除了英国普通法,新加坡还存在一个仅为穆斯林设立的单独的宗
教法庭体系。这个例子(以及其他很多例子)说明,法律传统始终在不
断发展,不断与各种传统融合,从而适应人口状况、地缘政治以及全球
化的变化要求。此外,明确划分各法律传统间的界限,并将一个国家的
司法实践归为其中某一种,也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古罗马民法传统
作为现存最古老的法律传统,罗马法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从公
元前6世纪这个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小共和国成立,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法
成为所有居住在意大利境内的人都需遵守的法律,再到公元3世纪成为
西起大西洋、东至幼发拉底河、北达英格兰和苏格兰、南及撒哈拉沙漠
边界的庞大帝国内所有自由民的律法。随着古罗马帝国扩张到古代世界
的遥远边陲,它也吸收了大量新律法,将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纳入了帝
国。
古罗马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古希腊人的学生,但说到法律,他们算得
上大师,为现代法律的发展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与其他大多数文明社
会类似,古罗马法律基于数世纪前的不成文习惯法,彼时,立法是上层
贵族的职权。由于法律由上等阶层把持,罪行与处罚对于普通古罗马人
而言始终神秘莫测。到了公元前5世纪,来自下层的反对派强迫立法者
将社会规则编写成法典,以平息人们的不满。于是,《十二表法》成了
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不幸的是,公示于古罗马广场上的原件已在公
元前390年高卢人攻占古罗马时被毁。我们能确知的是,这些法条当时
被刻于十块铜板之上,放在集市供所有人观看和了解。由于遗留的部分
残缺不全,我们只能从后世作品的众多引述中拼凑重现这部法典。相比
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法,早期罗马法更多涉及程序问题,它是现存最早
的、最重要的法规汇编。
《十二表法》规定了罪行及其相应的惩罚,为我们窥视早期古罗马
社会的文明提供了线索。该司法体系特别关注了在夜色掩护中实施的罪
行。事实上,用于描述偷窃的词furtum正是由furvus(黑暗的)衍生而
来,表明大多数偷窃发生在黑暗笼罩之下。绞刑适用于夜间在他人的庄
稼地里偷偷放牧的罪行;而对焚烧谷仓或谷堆的惩罚是将罪犯活活烧死。变节背叛的高级将领会被用三辆马车车裂。据说,国王宣称这
是“对全人类的警告”。[4]
流放是一种专为社会高等级成员保留的处罚手段;类似的罪行,低
等级成员则要被迫服劳役或被处死。流放分若干种不同形式。比方说,流刑只是将罪犯逐出特定地区,而驱逐出境则意味着不只被长期放逐,还要被剥夺公民身份,没收所有财产。公元1世纪,当涉及杀人罪时,无论是使用武器行凶、做伪证致人死亡还是下毒,贵族都会被处以上述
的流放之刑,而下层民众则没那么幸运,等待他们的是钉十字架或葬身
猛兽之口。[5]
古罗马人精心立法,同样也费心设计酷刑。彼时最著名的一种惩罚
是“袋刑”。这种刑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最初用于惩罚那些杀父
弑母的人。传统的做法是将鲜血淋淋的罪犯与一条狗、一只猴子、一条
蛇、一只公鸡或其他动物缝进皮革袋子里,然后将皮袋扔进河中或大水
池中。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公元前1世纪后期,庞培律废除袋刑,代之以火刑或被猛兽撕咬。[6]
此外,若古罗马公民按照“犹太礼仪”行割
礼或纵容其奴隶行割礼,将被剥夺所有财产并终生放逐孤岛,施行割礼
手术的医生则要被处死。
早期,对女性的处决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因为行刑前首先要剥去她
们的所有衣服。由于规定刽子手不得杀死处女,所以他们要先玷污女
犯。[7]
对其他罪犯的处决则是公开进行,手段包括活活焚烧、野兽撕
咬、丢进塔平岩(Tarpein rock,和希腊人的深坑处决差不多)等等。
公元1世纪和2世纪,角斗是古罗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恢宏的古
罗马斗兽场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昔日古罗马的辉煌。在那里,奴隶、罪犯
和职业角斗士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着生与死的搏斗,不是互相厮杀,就
是面对从帝国的偏远角落运来的猛兽。然而有一点并不为人所熟知,也
往往被导游刻意回避,即这座斗兽场作为行刑场所的核心角色已有200年之久。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称这种处决是“毫无技巧的屠杀”。但在古
罗马皇帝们看来,这是震慑民众的好机会,可以让他们牢牢记住至上的
古罗马统治者手握生死大权。罪犯们在行刑前夜被马车运来,关在位于
斗兽场地下臭气熏天的小屋里直至次日。罪犯们深知等待自己的将是怎
样的命运,试图自杀的人不在少数。根据塞内加的记载,一名奴隶把头
塞进车轮之间,碾碎了自己的脑袋,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结束了生命。[8]
中午时分,罪犯们被带入斗兽场,分成两组,具有古罗马公民身份
的一组,非公民和奴隶另一组。公民往往先行处决,且得益于他们的公
民身份,他们死得相对痛快些。有些是被刽子手一击致死。也有时,两
名古罗马公民会被一同送进斗兽场,一个人有武器,另一个人没有,有
武器的人要追赶那名赤手空拳的人并将其杀死。一旦完成,幸存者要交
出武器,然后被另一名罪犯追杀。这个过程如此重复下去,直到最后只
剩一名幸存者,而他将被刽子手处决。在此类处决中,施于非公民罪犯
的羞辱也同样落在公民罪犯身上。有时候,身为公民的罪犯会屈辱地与
奴隶一同受折磨。
处决公民罪犯之后,非公民和奴隶就要面对最残酷的死亡,且缓慢
的处决过程往往会占去大部分午休时间。他们被钉十字架,被活活烧
死,被野兽吞噬。这其中许多人是违反了神圣律法,杀人、纵火、亵渎
神殿。基督教作家们记载了大量被野兽撕咬的处决案例。别出心裁的杀
戮无穷无尽。有时,不同的行刑方式会结合使用。比如,奴隶有可能会
先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再被烧死;也有时,他们可能会被绑在某个位置
上,让猛兽恰好能撕咬他们的四肢。神话是古罗马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了打破千篇一律的传统处决方式,古罗马人也会上演各种致命
的神话,由罪犯充当牺牲者的角色。
至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钉十字架的处罚方式,这不仅是因为
其象征意义,也是因为围绕这种死刑有很多误解。多数意见认为,发明
钉十字架刑的是腓尼基人,但也有观点认为是波斯人。[9]
这种刑罚后来传入古希腊、亚述、埃及和古罗马。据估计,有数万人死于十字架上。
单单是古罗马,克拉苏皇帝就曾为庆祝胜利在一天之内钉死了6000人。
最初,钉十字架(“极痛苦的”[10]
一词的原型)是一种屈辱的死
法,通常用于处罚奴隶和重犯。在采用十字架刑之前,罪犯只是被简单
地绑在柱子上等死。十字架问世之后,曾有若干种不同的造型,有的是
四臂或三臂,还有的是X形结构。通常,受刑者会被剥去外衣,只留下
缠腰布,而在此之前,他们还要受鞭打,并被迫将十字架的主梁(整个
十字架的重量是一个人无法承受的)扛到行刑地。
近期的研究证实,无论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罪
犯其实都是“缓慢窒息”而亡。事实上,关于如何将罪犯固定在十字架
上,目前仍存在争论。1952年,一名法国物理学家发现,想从手掌处钉
住一名成年人是不可能的。通过使用尸体做试验,他发现,被钉子钉住
的手掌可承受的最大体重是40公斤,只要超过这个重量,手掌就会被撕
裂。通过排除法,剩下的方法要么是用钉子钉住腕骨(这样就能承受整
个身体的重量),要么是用绳子绑在十字架上。无论如何,最终的目标
是要让罪犯的身体悬挂在十字架上,缓慢窒息而死。当身体呈悬挂状态
时,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膈和肋间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受刑者只能吸
气(不能呼气),胸腔被越胀越大,最后窒息。这种折磨短则三四个小
时,长则四天。
1971年1月,以色列考古学家宣布他们已鉴定了一具名为约哈南
(Yehohanan,“约翰”的希伯来文写法)的犹太青年的骸骨。该遗骨在
1968年首次出土,很可能是公元1世纪时被钉十字架。这一发现为古代
地中海地区的十字架刑提供了首例铁证。大部分记录表明,十字架刑在
古罗马一直使用到4世纪,直到被君士坦丁大帝废除。然而,早前的证
据至多只是推测,因为人们虽在(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出土的)尸骸的前
臂和脚跟处发现孔洞,却从未能在附近找到钉子。约哈南的骸骨是在一
处埋遗骨的洞穴中被发现的,旁边还有另外几具骸骨。亚兰文字母拼写的名字已模糊难辨。令考古学家们兴奋的是,他的脚踝骨上穿着一根7
英寸长的锈迹斑斑的钉子。研究者分析,这根钉子之所以被留在原地,很可能是因为它被钉在了做十字架的橄榄木的硬节处,因此当锤子砸下
去时,钉子稍稍变形弯曲。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尼库·哈斯(Nicu
Hass)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约哈南之死的过程。按照传统,在经历一系
列死亡前奏之后,约哈南的下肢有可能受到棍子的致命一击,双腿折
断,随后的大出血和休克加速了他的死亡。事后,有人曾试图从十字架
上拔出弄弯的钉子以便移开尸体,但或许是出了什么岔子,固定尸体的
钉子顽固地埋在十字架里纹丝不动。哈斯认为,要将受刑者同十字架分
离,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砍断双足,然后将钉子、木块(用于固定罪犯的
脚)和脚一起从十字架上移开,之后按犹太习俗立刻安葬,以免尸体长
时间暴露在外。一系列事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方才有了这一前所未有
的发现。[11]
若论严刑峻法,古罗马暴君之中当首推卡利古拉,他的名字后来成
了残忍酷刑的代名词。据说他喜欢亲临刑场,边进餐边以此为乐。在一
次宴会上,他命令刽子手砍掉一名奴隶的双手,因为有人指控这个奴隶
偷了沙发上的银带子。之后,他又命人将断手系在那个奴隶的脖子上,在大厅环行示众。卡利古拉追求残酷,开创了惩罚的新境界。他在签署
处决名单前时常咕哝着“我在清理渣滓”。他偏爱共和国时期遗留下的火
刑(活活烧死),把斗兽场当作上演杀戮盛宴的舞台。在一次斗兽表演
期间,他以价格太高为由拒绝从屠夫手中买肉,因为反正有足够的罪犯
可以拿来喂野兽。据说,他站在柱廊间俯视着排成一行的罪犯,命令
道:“杀了那两个秃头之间的所有人!”[12]
有时,卡利古拉会强迫死刑
犯的父母眼睁睁看着儿子被处决。有一次,一名父亲声称自己病得很
重,无法亲自去看儿子被执行死刑,卡利古拉竟派人送去了担架。卡利
古拉的暴虐没有底线。一名士兵在被投入野兽之口前为自己的无辜申
辩,卡利古拉命令将罪犯带回来,似乎是要宽大为怀,谁知他只是将罪
犯的舌头扯下来,然后继续行刑。一名卡利古拉的传记作家称,如果有若干种处决手段可用,卡利古拉定会选择能造成无数小伤口、慢慢折磨
的方式,正如他本人说的“让他感受到死亡的降临”。面对人们的指责,卡利古拉回应说:“让他们尽情地恨我好了,只要他们惧怕我。”[13]
在提比略皇帝治下,所有罪状一律判死刑,且告发者的每一句话都
会被采信。有些被告由于确信只要出庭就会被判有罪,索性直接自杀,逃避注定将至的屈辱和痛苦。
公元4世纪,当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并奉其为国教之后,对性犯罪
和道德犯罪的惩罚比以往严厉了许多。昔日私下里的小过错成了要被公
之于众的罪行,且常常受到残酷的惩罚。以往,通奸者可能会被流放至
孤岛;但在基督教帝制时期,各类伤风败俗的性犯罪,包括通奸、兽
奸、乱伦和同性性行为,都成了死罪。不过,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对性
犯罪不再从轻处罚的现象,与其说仅仅是朝着古代《圣经》式处罚的转
变,倒更有可能是对一系列强奸和绑架案的回应。彼时,有些野心勃勃
的古罗马人试图用性侵行为达成与富家女性结婚的阴谋。[14]
无论如
何,与过去相比,将通奸、淫乱定为死罪的做法是一次明显的转变。在
古罗马帝国初期,通奸的定义为与“体面的已婚女性或寡妇”或“未婚且
不以卖淫为业的自由女性”发生性关系。[15]
对此的惩罚通常是剥夺已婚
女性的一半嫁妆以及三分之一的其他财产,并将其放逐到岛上,她的情
夫也会被剥夺一半财产并放逐到另一座岛上。涉案女性的父亲有权杀死
自己的女儿及其情夫,但前提条件是要在他女婿的家中当场抓奸,并将
他们双双杀死,一如戏剧中的情节。否则,如果做父亲的只杀了女儿的
情夫,就会被控谋杀。从本质上说,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被戴绿帽子的
丈夫及其家人不将案件移交法庭而自行实施报复。
或许早在公元3世纪初,当两名士兵因与一名女仆发生性关系而被
定罪时,马克里努斯皇帝(Emperor Macrinus,217—218年在位)就已
为后来的基督教式惩罚开了先河。由于这名女仆身为娼妓,士兵们的行
为本不触及通奸法令,但仍遭到了审判。皇帝命令划开两头阉牛的身体,趁牛还活着的时候把这两名士兵分别塞进牛身里,只把脑袋露在外
面,以便他们能相互交谈。根据一名历史学家的记载,由于他们的行为
并没有实际违反任何法律,因此受到了从任何书本里也找不出的“独一
无二的惩罚”。[16]
作为罗马法的基础,十二表法直到近10个世纪之后才被查士丁尼的
《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取代。在尤里安大帝(Emperor
Julian)治下,罗马法发展到了顶峰。此时的罗马法将1000年的法律实
践整合进条理清晰的系统中,兼顾了简明与公平。这部法典是后来大多
数欧洲(及其殖民地)民法典的基础。然而,正如一名法律历史学家指
出的,其中的刑法部分“仅仅是以一种异常古怪的形式影响了现代欧
洲”。[17]
无论如何,527—565年查士丁尼的统治标志着由古代向中世纪
的转型,他所开启的时代将一直延续到现代欧洲的诞生。[18]
但古罗马
文化早在中世纪欧洲国家成形前就将土崩瓦解。
随着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日耳曼部族,也就是古罗马人
所说的那些生活在古罗马帝国之外的蛮族,以国家的形式登上了世界政
治的舞台。日耳曼部族是早期欧洲律法汇编的重要催化剂。在欧洲大
陆,法兰克人在北高卢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国,东
哥特人在意大利建国,勃艮第人在高卢东南建国(不久就被法兰克人征
服),汪达尔人则在北非建国。其中,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
贡献了最有实质意义的法律材料,且相互之间影响颇深。截至目前,后
期日耳曼部族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正是出自法兰克语文献,且被认为是除
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典之外的所有蛮族法律中最具日耳曼特色的。[19]
在这些法令中,最著名的当属6世纪第一个10年间编纂的《萨利克法
典》(Salic Code)。彼时,法兰克人在北高卢建立了存续时间最长的
蛮族王国之一。法兰克法律是受古罗马影响最小、最具日耳曼特色的部
落法典。与罗马法不同,该法典没有关注婚姻、家庭、遗产、赠物和契
约,而是为诸如杀害女性和儿童、“击打头部致头颅破碎”或“未经马主同意私自剥死马皮”等各种危害行为确立了固定的货币处罚和其他类型
惩罚。《萨利克法典》中有很大篇幅涉及暴力犯罪、杀人和偷盗。我们
从法典中可以确知,一个人的财产及其本人皆可被当作犯罪赔偿的最终
抵押物,而罚款则适用于偷盗“蜂群、狗、牛、家禽、山羊、绵羊和奴
隶”的行为。通常情况下,自由民可以支付罚金,而犯了偷窃罪的奴隶
则会被处120鞭甚至阉割之刑。
《萨利克法典》的一大特色在于量刑完全取决于身价,即依受害者
和罪犯的身份来确定罚金,该制度后来在公元5、6世纪时被德国入侵者
带到了英国。每个人都有其“身价”。比方说,如果任何人杀了为国王效
力的人,会被罚24000第纳尔;如果杀了一名法兰克自由民或受《萨利
克法典》管辖的野蛮人,会被罚8000第纳尔。如果所犯罪行是暴力袭击
的话,具体处罚取决于攻击的程度和涉及的人员。根据《萨利克法
典》,“如果任何人殴打另一人的头颅导致头顶的三块颅骨破裂、脑浆
毕现,袭击者将被罚1200第纳尔”。如果有人被打断肋骨“造成开放性伤
口并伤及内脏”,相应的罚款是1200第纳尔;如果只有血“滴落在地
上”,罚金是600第纳尔。若是奴隶犯法,惩罚要严厉得多。奴隶若偷盗
价值2第纳尔的物品,一经发现,不仅要赔偿,还要被按在地上打120
棍;若偷盗价值40第纳尔的物品,则会被阉割或判罚6先令。[20]英国普通法传统
从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英国受到来自北海对岸的日耳曼和斯堪
的纳维亚移民的侵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盎格鲁部族、撒克逊部族
和朱特部族逐渐融合,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事实上,英格兰
(England)这个名称正是得自“盎格鲁人的土地”(Land of the
Angles)。在这片昔日古罗马帝国的北部边陲,400年来古罗马推行基
督教的失败尝试几乎未留下任何痕迹。公元410年,古罗马军队撤离,罗马法典也从当地人的记忆中随之消散。从彼时直到1066年诺曼人入侵
前,日耳曼传统给英国地区的犯罪与惩罚制度带来了最强烈的冲击。同
彼时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最根本
的法律思想之一是人皆有价,即“身价”。有100多条法律条款列举了各
类罚金,涉及从谋杀到点滴不和的方方面面。法律规定了身体每个部位
的价值,比方说一只眼睛值半个人的身价;损坏一颗牙的赔偿是16先
令,但后臼齿只值半价。打一拳赔偿3先令,扇一巴掌则是两倍赔偿。
在大多数人看来,被掌掴的人既受了侮辱又受了伤害,可谓双倍倒霉。
到了7世纪,英国成了武装贵族精英领导下的诸多小侯国的大杂
烩,基督教得以在此生根发芽。星罗棋布的小王国起起落落,直到公元
9世纪初才出现了若干个较为稳定的国家。在此期间,为了避免暴力循
环和世族仇杀,法律规定对杀人罪的惩罚是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赎罪金。
梅特兰(Maitland)和波洛克(Pollock)在其关于英国法律史的经
典著作中指出,日耳曼入侵者“不擅文字”,且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时
代也不甚清晰。[21]
约公元6世纪的根特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 of
Kent)颁布律法——当时的人们称为法令——是第一部日耳曼成文法,其中大部分涉及暴力犯罪和牛马盗窃罪。除了规定身价金,这部盎格
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法典也采用了一些监禁方式来处罚偷盗、行巫术之类的罪行,但最常见的刑罚仍体现了欧洲大陆特色,比如断肢、死刑
或放逐。自5世纪起,绞刑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的主要处决方
式。绞刑作为主要的处决方式被一直沿用到20世纪,尽管在诺曼时代早
期曾短暂地遭弃。在诺曼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执行绞刑的过程毫无技
术可言,受刑人得被慢慢勒死,而不是利用身体下坠时的重力和绞索结
折断脖颈子速死亡。从缓慢勒死到利用位于绞索结折断脖子,这个较人
道的方法改进花费了刽子手们几个世纪的时间。
在现代刑法制度出现以前,几乎不存在什么审判程序。影响了日后
正式审判程序的大量实践均来自欧洲诸日耳曼王国,例如神裁和辩护
人,也就是誓言帮手(愿意为你的人品发誓担保的人)。上述这两种做
法均来源于这样一个信念:上帝将站在正义的一方。自从日耳曼部族将
这些基于上帝审判的做法从欧洲大陆带到英国,直到1066年诺曼人入侵
之前,当地人一直依靠这套简单易行的方法进行裁决。
正如前一章所述,回顾历史,在不同的社会中,我们都可以见到某
类神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用火或水来审判在英国最常见,且审
讯通常在牧师的协助下完成。曾经做过伪证或无法提供足量誓言帮手的
罪犯必须接受神裁。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13世纪,其理念基础在于相信
上帝会保护无辜者。在实践中,神裁是终极审判,人们希望罪犯能在走
到这一步之前就坦白。火审有若干形式。有时候,被告要被蒙住眼睛走
过滚烫的木炭或炽热的金属。有时候也会用“浸锅法”,要求被告将手伸
进盛着沸水的大锅,并从锅里取出一块石头或约1磅(约0.45公斤)重
的东西。如果被告的手或脚在神裁三天后依旧化脓未愈,则被判有罪。
在另一些情况下,被告会被投入水中,沉下去就是无辜,浮上来是有
罪。杀人、伪造、行巫术、信奉异端邪说等罪行往往会用这种方式审
判。
判定有罪或无辜的第二种重要方法是使用誓言帮手。在这种情况
下,原告和被告都要提供誓言帮手来担保本方主张的真实性。誓言帮手的人数取决于身份等级和案件的严重程度。那些拒绝进行宣誓采证、神
裁或拒绝连续四天出庭的人会被剥夺法律权益,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再受
到法律保护,可以被追杀。剥夺法律权益的手段可以适用于回避司法机
构、拒绝支付罚金、拒绝出庭或潜逃的人。此外,这些人也会被剥夺所
有财产和公民权利。梅特兰和波洛克把剥夺法律权益称为“野蛮时代的
死刑”。[22]
一旦失去法律权益,一个人注定会同他所在的社群发生冲
突,而周遭的人也会攻击他。在13世纪以前,驱逐被剥夺法律权益的
人,焚烧其住所,毁坏其田地,对其追杀到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
有些罪行,比如叛国或暗杀,是罪无可恕的,除非被告能提供足够
多的誓言帮手或通过更严苛的神裁考验,比如从沸水中取出3磅(约
1.36公斤)重物(而非通常的1磅)。此外,常规神裁中要求沸水没过
手腕,更严苛的神裁要求沸水没过手肘。未能通过神裁意味着将被处
决。而在诬告、习惯性犯罪等较轻的案件中,未通过神裁的人将被判断
肢刑或肉刑。
日耳曼部族钟情“容易辨识的”惩罚手段,比如对诬告者割舌,对发
伪誓者斩断右手。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前,盎格鲁-撒克逊的主要刑
罚包括绞刑、火刑、溺毙、石刑、深坑处决、割耳、削鼻、割上唇、剁
手、剁足、宫刑、笞打和卖作奴隶。有趣的是,以囚禁为目的的建筑未
被提及。或许,正如梅特兰和波洛克指出的:“对于一个没有监狱和收
容设施的国家而言,最简单的惩罚方式就是处死。”[23]
根据6世纪的《埃塞尔伯特律法》(Laws of Ethelbert),逃犯在特
定条件下可以向教堂寻求庇护,这些条件包括向神职人员忏悔罪行、交
出所有武器、向教堂支付费用、坦白犯罪细节。罪犯可以得到40天的庇
护,之后要面见coroner
[24]
并发誓从此流亡。在离开故土的过程中,罪
犯会被安全地指引到最近的海港。不同于被剥夺法律权益者,自愿流亡
者可以穿着白袍,带着木十字架,以免受各种侵害。但流亡者一路上不得在任何地方停留超过两晚。到了16世纪,亨利八世要求给流亡者打上
易于辨认的烙印,以防这些人在没有得到宽恕的情况下返回英格兰。这
项规定在诺曼时代剩余的时间里一直得到奉行,直到1623年被国王詹姆
士一世废止。
公元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循着残暴的丹麦维京海盗的航迹,在从泰晤士河一直延伸到利物浦的一片被称为丹麦法区的地方安了家
(也将“法律”这个词引入了英语词典)。他们带来了具有浓厚的斯堪的
纳维亚宗教色彩的风俗,比如将罪犯勒在长木棍上并反复扎刺直至其死
亡。这个向奥丁表达敬意的习俗称为galgatra,或称绞刑树。在随后的
一个世纪里,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与附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混杂,其各自的律法和制度也相互融合,形成了英国文化。
英国历史以及普通法传统形成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是居住在法国北部
的诺曼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格兰的入侵。1066年,威廉一世、诺
曼底公爵的军队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大获全胜,完成了对英格兰的征服。
按照当时的传统,被征服地的民众通常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
为了赢得新臣民的支持,威廉一世顺势而行,沿用了大部分盎格鲁-撒
克逊司法制度,同时又从欧洲大陆引入了诺曼习惯法。他最突出的一项
改革是采用断肢刑而避免死刑。在此后的40年间,绞刑一度销声匿迹。
不过,这项措施未能防止大量罪犯在被挖眼或阉割后死亡。
诺曼人带来了很多新元素,其中包括设立治安官、coroner、法警、太平绅士和执行官职位,这些革新后来成了刑事审判体系中家喻户晓的
部分,并影响着英国普通法传统。比如1194年开始设立的郡级coroner一
职,负责调查死因可疑的案件和入室案。最早记载于拉丁文和法文史料
的宵禁在当时已存在了数个世纪,成为上等阶层限制下等民众活动的主
要手段。威廉一世则赋予了宵禁更神秘的色彩,用它来防范时刻存在的
火灾隐患。在那个广泛使用木材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预防措
施。但事实上,这一手段更有可能是为了防止盎格鲁-撒克逊反叛者利用寒冷的夜间时光秘密集会。每晚8点,当宵禁钟声敲响时,所有的火
都要熄灭,违者将面临严厉惩罚。
诺曼人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裁定有罪或无辜的各种方式之外增加
了一种新的神裁方式——决斗审判。早在诺曼人攻占英格兰之前5个世
纪,决斗——源于拉丁词语duellum(两个人之间的战争)——在日耳
曼勃艮第人中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用一名先王的话说,“每个人
都应时刻准备用剑来护卫他所坚持的真相,并服从上帝的裁决”。决斗
规定允许神职人员、女性和残疾人雇用代理人或帮手出战,只要他们发
誓不使用魔法或毒药。在大多数情况下,上等人使用马上决斗,下等人
则徒步决斗。如果被告能在决斗场上从日出坚持到日落,就会被裁定无
罪,原告会被绞死。在1096年的一起著名的决斗审判中,原告控告伊尤
伯爵密谋反叛国王威廉二世。国王本人亲临现场。伯爵决斗失败,被处
阉刑并挖去双眼。对决斗场地进行改进之后,比武审判变得更加实用,且规定不再允许雇用代理人。如果一名女性在审判中要对战一名男性,该男性必须站在齐腰深的坑里,该女性在坑外用拴着石头的皮带进行攻
击,男性则用棍棒还击。如果该男性三次未能击中女性,就意味着该女
性是无辜的。[25]
诺曼人攻占英格兰100年后,英格兰的犯罪问题越发严重。于是,亨利二世于1166年颁布《克拉伦登敕令》(Assize of Clarendon),建立
了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员要提交本地所有已知的罪犯名单,对他们进行
拷问。一旦被判定有罪,罪犯将受到严酷惩处,以儆效尤。所有没能通
过拷问的人都会被处以绞刑,或被砍掉一只脚并流放40天。10年之后,也就是1176年,《北安普敦敕令》(Assize of Northampton)规定了更
为严厉的刑罚,包括(在拷问定罪之后)砍断右手和右脚。
《克拉伦登敕令》也极大地促进了监狱建设。威廉一世是这一变化
的引领者,在他的推动下,英国修建了第一座皇家监狱——伦敦塔。不
过,这座监狱主要是用于关押国王的敌手。除伦敦塔之外,当时还有另几座专门羁押所。到了亨利二世时期,《克拉伦登敕令》要求治安官在
各郡修建监狱,关押所有等待皇家巡回法官审判的重犯。自13世纪后期
以来,随着监狱的增加,被处监禁的罪行种类也越来越多。
被誉为“普通法之父”的亨利二世设立了巡回法官一职。这些法官定
期巡视英格兰各地,通过使用标准程序处理案件,旨在最终让“普通
法”通行于全国。与大多数前现代法律传统一样,习俗曾在英国各地的
地方法庭裁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地理因素和涉案人的社会地位千
差万别,它们常常给法官带来困扰。在随后的几年中,基于国王法庭大
法官裁决的法体日趋成形。渐渐地,这些法律,或称普通法,与丹麦、日耳曼法律主导的那些地区的法规形成了明显差异。随着新判例的增
加,法官们开始引用类似判例作为参考。这种做法确立了先例在审判中
的重要性,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规则,它们不仅适用于英国,也适
用于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伊斯兰法律传统
7世纪下半叶,与条顿蛮族入侵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大约同一时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作为罪与罚这一主题的后来者,其后几个
世纪里形成的伊斯兰法律传统在随后的1400年间逐渐传播至北非、中亚
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地区的大部分惩罚主要遵循
同态报复的原则,“很好地满足了游牧社会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需
要”。在没有法律体系和国家概念的环境中,亲族协同成了社会最强有
力的纽带。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约公元570年,公元610年左右开始传
教,但伊斯兰律法直到公元8世纪才开始形成。[26]
早期的伊斯兰律法在
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阿拉伯文化的遗产。与摩西律法相似,伊斯兰法律传
统也是一种神权法律体系,基于神通过圣典授法于先知的信仰。不过,犹太律法的发展从未能达到伊斯兰律法的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
于犹太人屡屡被监禁和驱逐的命运。
根据伊斯兰律法,犯罪指的是“行被禁之行或疏于应尽之责”。[27]
这个定义与西方实证法中的定义“违反公法并会受到以国家名义实施的
惩罚的主动行为”[28]
差不多。伊斯兰的司法实践始终强调双重保护,既
尊重被告人权利,也重视对社会的保护。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发生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的一个现代案例来说明。一名索马里军阀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命人把失手杀死了一个平民的士兵送到受害者家
中,“迅速对其头部开枪”。军阀无意间对采访者说道:“这是伊斯兰法
律。这让公众满意。”[29]
伊斯兰法律传统最重要的两个来源是《古兰经》中的伊斯兰教法
(Sharia)和圣行(Sunna)。被视为“《古兰经》外经”的圣行由阿拉伯
习俗和先知的生平事迹构成。伊斯兰教法则是来自真主的不容亵渎的律法。从西方观点看来,它似乎不像法典那般包罗万象,结构上也较松
散。作为法律典籍,它的一大弱点在于,既然是真主所定,那就既不能
改变亦不能增补。此外,由于《古兰经》刑法的形成年代太早,如果想
适用于当代的刑事审判,即便绝非不可能,也有相当难度。
诠释先知遗训的任务落在了乌力马(ulama,或称法律专家)的身
上,他们自中世纪起就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同基督教的
神职人员没什么不同。公元900年,乌力马认定伊斯兰教法是完备的,无须再做更多的诠释。人们很难概括伊斯兰律法的发展,原因之一就在
于,穆罕默德死后的若干世纪里出现了四大伊斯兰法律学派,每一派都
对法律做出了不同的诠释。这四大学派各自以其创始学者的名字命名,有的宽容开明,有的则坚持宗教激进主义。这其中最开明的当属哈乃斐
学派(Hanafi),他们意识到,社会在改变,创造各种法律的环境也在
改变,因此“律法并非不可改变”。发源于伊拉克的哈乃斐学派在漫长的
奥斯曼人统治期间因诠释律法而声名卓著,它也是如今印度大部分地
区、巴基斯坦以及除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其他几个中东国家的官方学派。
态度最严格、最保守的是罕百里学派(Hanbali),它对其余三派的任何
创新都一概反对。该学派如今活跃在沙特阿拉伯。
在穆斯林刑法中,罪行分成三大类,相应的惩罚是由《古兰经》确
定还是由法官决断各有不同。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须给予强制惩罚,因
此适用罚戒重罪的伊斯兰教法,且不得宽恕、调解或开脱,相应的惩罚
也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行的规定。对罪犯的惩罚方式以肉刑为主,但与终身监禁和西方国家使用的其他惩罚手段不同,伊斯兰教法的行刑
过程迅速、公开,且只给罪犯带来短暂的痛苦。[30]
比如,若窃贼被判
削手,医生通常会事先为他们施麻醉,然后用利刃行刑。究竟何种罪行
要依伊斯兰教法判决,目前并没有共识,但绝大多数资料显示,伊斯兰
教法涉及的罪行主要包括通奸、偷窃、抢劫和诽谤、通奸或发生非法性
关系,也就是主动与配偶(无论是否已婚)之外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不过,近来伊斯兰教法已对涉案一方是否已婚做出了区分。若性接触的程度仅限于男性器官插入女性器官,具体惩罚可依情酌定。正如上一章
提到的,各社会十分重视保护和维护信众中清白、高尚的血统。有罪一
方的身份不同,犯通奸罪的惩罚也不同。通常,对已婚者的惩罚是石
刑,对未婚者则处100下鞭刑。
关于伊斯兰法律传统中的石刑,在此有必要附上一笔。与伊斯兰法
律本身一样,石刑基于早前的习俗,尤其是《旧约》里提到的摩西用石
刑惩罚不守安息日的人。从公元1世纪起,犹太教法将石刑定为对一系
列违法行为的惩罚手段,并详细规定了行刑方式。不过,对于石刑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应用,我们只能凭借推测。
石刑并没有记载于《古兰经》,但出现在关于伊斯兰律法传统的圣
言录中,并被明确规定为对通奸行为的惩罚手段。直到2007年,伊拉克
库尔德雅兹迪教派聚居区仍有石刑处罚的案例。西方人或许认为石刑野
蛮残忍,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石刑符合穆罕默德时代阿
拉伯社会的价值观。纵观历史,人们在实施刑事处罚时往往雷声大雨点
小,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警告”,而非结结实实的惩罚。
不经允许转移他人财物并意欲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偷窃。该类行为的
严重性通常取决于偷窃的价值和手法。尽管如此,伊斯兰教法规
定:“偷窃者,无论男女,一律砍断双手。”为了起到震慑作用,行刑通
常公开进行。不过,被窃物品应具有最基本的价值,如果偷窃的是酒、猪肉等在伊斯兰教义中毫无价值的东西,则无须受断手刑罚。
抢劫,即武装抢劫或拦路抢劫,由于使用了强迫和埋伏手段,被视
作更为严重的罪行。《古兰经》对此类罪行的惩罚是“处死、钉十字
架、手脚交互割去(交叉断肢)或驱逐出境”。有一种司法解释认为,法官在判决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决定具体
的惩罚手段。但大多数解释认为,实施何种处罚完全取决于罪行的严重
程度,法官并没有自由裁量权。杀人者将死于剑下;偷窃者将被交互断
肢(斩断右手和左脚);使用暴力威胁但并没有杀人或偷窃的,被处驱逐出境(或监禁);同时犯有偷窃和杀人罪的将被钉十字架。同斩首一
样,断肢刑也用剑或弯刀执行。不过,关于钉十字架的方式仍存在争
论。大多数人认为,抢劫犯会被活生生钉上十字架,然后用长矛刺死。
另一些人则认为,罪犯会先被处决,然后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任
凭风吹日晒,以此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和震慑。既谋财又害命的土匪将
被斩首,陈尸十字架。如果仅仅杀了人但没有偷窃,则判单纯斩首。总
之,侵害商贸和旅行的行为绝不能轻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相应的刑
罚如此严酷且要公开进行。
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第四种罪行是诽谤,也就是诬陷他人有不道德行
为。要证明一起通奸案,必须有四名男性证人对目击的情况做出清晰描
述。如果其中三个人的证词对被告不利,但有一名证人不能证实该行
为,则另三人将受惩罚。比如说,若一名女性被控通奸,但控诉人无法
依照法律要求提供四名证人,便属于诽谤。对诽谤罪的惩罚是鞭打80
下。
归属于同态复仇类惩罚的罪行,或称“血腥”犯罪,通常是指有意或
无意地伤害他人的躯体。和这个概念相似的现代法律术语是“人身伤害
罪”,包括谋杀、主动或被动杀人、故意或非故意的人身伤害、致人伤
残。对此类罪行的惩罚有两种方式。同态复仇惩罚只适用于针对人身的
故意伤害,且需证据确凿。同态复仇在伊斯兰教法中由来已久,目的是
要满足受害者及其家人寻求报复的普遍心理,同时避免报复过度,不致
引发世仇和更多暴力。在此情况下,同等程度的复仇是被法律允许的,这与《汉穆拉比法典》以及后来的希伯来法律中感同身受、刑同其害的
原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回事。但与《汉穆拉比法典》不同的是,根据伊
斯兰教法,如果有人放火烧了他人的房屋,受害人不能用同样的手法实
施报复,否则便会受到处罚。另一种惩罚方式是支付赔偿金,即向受害
者或其家庭支付赔偿,该方式适用于非故意伤害罪,包括被动杀人和非
故意伤害。最初,赔偿金的数量是一定的,不依社会经济地位而变。大
部分学者认为,对女性的赔偿金是男性的一半。按照举证要求,使用赔偿金惩罚之前必须证明被告人神志清醒且做出犯罪行为时是出于自愿。
因此,想寻求同态复仇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做出适宜
的复仇行动,否则就要由专业行刑者代劳。同态复仇的限度在于施予罪
犯的痛苦不能比受害人遭受的更大。如果缺少确凿证据,则只能适用赔
偿金处罚。
第三大类,也是最轻的一类是可判酌定刑的罪行,主要指的是《古
兰经》或圣行没有规定惩罚方式的犯罪行为。有阿拉伯学者认为,酌定
刑惩罚比伊斯兰教法或同态复仇规定的惩罚更严厉,因为后者有预先规
定且惩罚是有限度的,而酌定惩罚则完全由法官决定。在此方式
下,“一个人有可能被反复鞭笞,直到完成必要的忏悔或赎罪”。[31]
可
处以酌定刑的罪行包括小偷小摸、通奸未遂、同性恋行为、强奸以及其
他伊斯兰教法禁止但并未规定相应惩罚措施的行为。因此,对被控吃猪
肉、做伪证、放高利贷、饮酒、在秤上做手脚者的惩罚各有不同。既然
惩罚方式由法官或统治者决定,他们就要首先考虑罪行的严重性,然后
考虑罪犯本身的人品、犯罪记录、生活方式和最终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此类罪行很少会被处死,但遭鞭笞极为常见,这对罪犯本人和社会都是
最好的选择。鞭刑受青睐的原因在于执行迅速,能让罪犯——通常是其
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返回工作岗位养活家人。不使用监禁手段,罪
犯的家庭就不会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罪犯个人也不会受到监狱里其他
罪犯的负面影响。鞭笞刑的下限是三鞭,上限说法不一,但通常为39至
75鞭不等。有一则故事或许可以说明法官在处理酌定刑时如何灵活地行
使自由裁量权。也门的首任总督用葡萄酒招待宾客,然后对那些喝醉了
的人提起控诉。当客人们提出抗议时,他解释说:“我惩罚的不是饮
酒,而是醉酒。”哈乃斐学派只禁止饮用葡萄酒,因为那是先知时代唯
一可得的酒类,其他种类的酒精(或毒品)只要不至于使人沉迷,就未
必会被禁止。
就很多方面而言,酌定刑似乎更现代。某些行为并没有相应的具体
惩罚,但这些行为的确不是穆斯林应有之举,酌定刑的运用使得伊斯兰教法既可以“发展并应对现代生活的新需求”,同时仍然能满足穆斯林社
会的要求。调和中世纪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之间差异的困难可以从最近的
一个案例中窥见一斑。一名沙特女性因违反本国禁止女性驾车的禁令被
判鞭笞10下。作为全世界唯一不允许女性开车的国家,那里的很多家庭
被迫雇用驻家司机。然而每月至少300美元的额外开支超出了大多数家
庭的经济能力,因此女性不得不依赖男性亲属送她们上学、就医和购
物。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成文法规定女性不得开车,但按
照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有必要设立限制自由和活动的禁令,从而让女
性远离罪恶。抗议者指责当局因驾车鞭笞女性,因为对交通违法行为的
惩罚至多不过是罚款而已,于是有人说:“就连先知的妻子们也骑骆
驼,骑马,因为那是唯一的通行方式。”在此要为警方辩解的是,尽管
警方的确会拦下开车的女性,但通常只是询问而已,并在她们签署不再
开车的保证书后便放行。巧的是,那名被判鞭刑的女性当时正在参加一
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因此这顿鞭刑有可能是来自宗教强硬派的报
复。[32]现代世界的伊斯兰教法
从现代观点来看,保守的伊斯兰法律往往被视为既严酷又不合时
宜。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政权抛弃了伊斯兰法律中的实证思想,背离了伊
斯兰教义和精神。不幸的是,在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尼日利亚和阿富汗这些用伊斯兰律法取代了更开明的世俗法律的国家
里,伊斯兰教法中不太人道的一面愈演愈烈,尤其是有些惩罚的确源自
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刑罚体系。石刑是这一类惩罚中最常被提及、最
容易被误会的一种。伊斯兰法律和其他习俗的设计初衷是要保护男性血
统、家庭、荣誉和财产。在部族社会里,族长掌握着孩子的血统关系。
性犯罪之所以要被处以石刑(而非其他形式的处决),乃是因为人们认
为此类罪行辱没了族群的血统,因此要由部族成员共同惩罚。与其他惩
罚手段不同,被家人、旧日好友和邻居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石头砸死,对
罪犯而言一定相当可怕。人们希望这样的判决能够杀鸡儆猴,减少引发
亲子关系问题、威胁部族血统完整的犯罪行为。
以下是伊斯兰教法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几个应用案例。伊朗的伊斯兰
教法禁止放高利贷行为,任何放贷牟利的人都会被判处74鞭以及最长3
年的监禁。此外,法令还规定,初犯者要被剁掉右手的4根手指,再犯
者剁掉脚趾,第三次犯则要被终身监禁。一个案例体现了同态惩罚的持
久影响力。2011年,一名伊朗男子因将一桶硫酸泼在一名拒绝与他结婚
的女性脸上而被定罪,并被判以相同的方式弄瞎双眼。[33]
此案发生在
2004年,受害人在攻击中失明,容貌被毁。她有权宽恕攻击者,但她不
顾国际人权组织和英国政府的呼吁,拒绝原谅他的罪行。她的理由是,惩罚乃是对其他打算做类似行为的人的警告。2008年,伊朗的一个法
庭“同意受害者的要求,依据伊斯兰法理允许受害者向罪犯寻求报复”,下令在该犯的每只眼中滴入5滴相同的化学品。只有受害者本人才能以宽恕罪犯的方式阻止判决。[34]
沙特阿拉伯仍使用斩首作为处决方式,侨居利雅得的外国人把行刑
的地点译作“咔嚓咔嚓广场”。在那里,刽子手用4英尺长的弯刀公开行
刑,血水通过一个小小的金属阴沟盖流进下水道。
1983年9月的一天,气温一如往常达到近38℃,数千名苏丹人聚集
在喀土穆城北一所监狱的庭院内,焦急地等待观看伊斯兰式行刑。两名
因偷窃获罪的男子坐在椅子上,脸上蒙着白布,准备接受传统惩罚。行
刑前,焦躁的人群聆听了对这两人的指控。《古兰经》中关于非法占有
的韵文被大声念诵,人群齐声高呼:“真主是伟大的!”接着,持刀的行
刑者出现了,麻利地砍下了两名罪犯的右手。令人惊讶的是,罪犯几乎
没有流多少血。观察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上臂扎了止血带。对于其
中一名罪犯而言,这还不算完。此人是尼日利亚移民,下个月,他还要
被砍掉一条腿。[35]
1996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伊斯兰教法庭判决一名菲律宾女
佣受罚100鞭,罪名是她刺死了雇主。鞭刑分5天进行,每天执行20鞭。
当地官员说,这只是象征性的惩罚,行刑者在胳膊下垫了一本书以减轻
抽打的力度。尽管女佣声称前雇主企图强奸她,自己只是在自卫,但仍
免不了被判鞭刑并处一年监禁,之后被驱逐出境。
有很多伊斯兰教法的支持者将本地的低犯罪率与非伊斯兰教法地区
的高犯罪率对比,声称这是伊斯兰律法的功劳。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
为这些国家的犯罪数据很少拿出来与世界其他地区共享。不过,有一个
地方的确可以体现出伊斯兰教法的作用,那就是1996年的索马里。当
时,摩加迪沙(Mogadishu)到处都是家族仇杀、强奸、抢劫以及——
用一名《纽约时报》记者的话说——“宛如世界末日后的”随意杀人。走
投无路之下,一所伊斯兰教法法庭临危受命,将首都部分地区由“无法
无天之地变成了相对安全、文明的区域”。如果说有人对平息犯罪潮的方法有任何质疑的话,那主要是针对砍掉本地窃贼手足(在不使用麻醉
的情况下公开行刑),并置于本地体育场前示众的做法。[36]
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间,塔利班用伊斯兰法律的
极端版本完成了“自我定义”。随着该组织在阿富汗的壮大,他们也向世
人展现了自己的伊斯兰法律。与大众认知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
上台之前,对通奸犯行石刑的做法在阿富汗并不常见。而那些确实使用
石刑的案例均有严格的宗教监督,且首先进行了公正的审判,并由宗教
学者为惩罚设定限制。按照规定,石头应体积较小,参与行刑的人在投
掷时手臂抬起的高度不得超过头。最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合法的法庭来
完成。在2010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对夫妇因私奔被石刑处死,行刑地点
位于一个村落里,没有政府监督。一名教派长老指责这起石刑违法,指
出“用大石头非法处决是错误的”。[37]
在2010年的一起案件中,昆都士省(Kunduz Province)的数百名村
民参与了处死一对年轻人的石刑。但在更多情况下,尤其是如果涉事男
性属于塔利班组织或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石刑只会落在女性身上。有
时候,同性恋会被迫站在砖墙前,被推倒的砖墙砸死。塔利班极尽严格
地践行伊斯兰教法,对宽恕问题亦不例外。1999年,一名男同性恋被判
死刑,具 ......
[美]米切尔·P. 罗斯 著
胡萌琦 译
中信出版集团目录
引文
引言
第一章 罪与罚:太初
第二章 法律传统的兴起
第三章 变化中的犯罪:从封建制度到城市和国家
第四章 惩罚的转变与监狱的兴起
第五章 路匪、土匪、强盗和绿林好汉:贼帮和早期有
组织犯罪
第六章 禁令、海盗、奴隶贩子、毒品走私犯和犯罪全
球化
第七章 现代谋杀
第八章 后殖民社会的罪与罚
第九章 21世纪的罪与罚
参考书目致谢
版权页引文
本书献给数千年来所有遭受
不公正的指控、审判和惩罚的人引言
往昔未逝,往昔犹存。
——威廉·福克纳,《修女安魂曲》,第一幕,第三场(1951年)
往昔俨然是另一个国度,彼时的人们行事古怪。
——莱斯利·珀斯·哈特利,《中间人》(1953年)
2006年,国际新闻界再次被几个监狱系统中的不寻常事件搅得沸沸
扬扬。你一定以为接下来会听到一个困顿绝望的悲惨故事。又有谁听说
过“令人愉悦”的监狱故事呢?在大多数情况下,第一种反应是恰当的,毕竟,人们对监狱的认识——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如今的——总是同饥
饿、肮脏、混乱、暴力、堕落、帮派以及其他恶行画等号。不过,这一
次是一段被关在瑞典监狱里的三名以色列罪犯的极不寻常的小插曲。通
常,罪犯,尤其是被囚禁在海外的以色列罪犯,会寻求一切能从国外监
狱被遣送回国的机会。然而,当这三名罪犯面对如此安排时,却都以更
青睐北欧监狱的条件为由拒绝了,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享受“牛排、性生活和播放世界杯的免费私人电视”。如果这些听上去还不够诱人的
话,那就再看看这些“五星酒店级”监狱的其他福利吧。首先是上面提到
的牛排、免费有线电视,以及为期三天并提供狱内豪华公寓的夫妻探访
日。此外,不仅每名罪犯享有独立房间,而且还有各种便利设施,每年
还可以(在警车的陪同下)在斯德哥尔摩逛两次街。[1]之所以选择这个故事,是因为它在微观层面上展现了同一时期、同
一类型的惩罚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里的差异。这两个国家都处于发达
国家的前列。今时今日,处在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刑罚上尚且迥然有
别,若纵观古今,放眼全球,不同种类的犯罪与惩罚间的差异想必会更
明显。监狱和监禁概念在18世纪理性时代的出现,是全球犯罪与惩罚史
上的里程碑。能施加在人体上的痛苦纵然有其极限,对监禁的理解却在
全球范围内以各种形式继续发展和演变,且其发展和演变仅受限于资
金、技术和创造力。21世纪瑞典和以色列监狱的例子仅仅让我们对全球
犯罪与惩罚的故事有了匆匆一瞥。不过,我们会继续深入下去。
本书将带领读者展开一段间或令人不那么舒服的旅程,穿越罪与罚
的演变。这趟旅行恐怕并不适合时间旅行者,因为途中充满了古往今来
的斩首、绞刑、石刑和其他可怕的刑罚。研究特定国家、宗教、地区和
大陆的犯罪与惩罚史的佳作不在少数,但除了多卷本的参考书之外,还
没有哪本书试图从全球视角考察该话题。本书中的历史叙事则广泛考察
了数千年来罪与罚的发展。
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惩罚(在历史或书面记录中)被定义为一种通
常由国家施加给违法者的强制性处罚。在历史上,罪的概念曾与恶的概
念相伴相生。从恶行与善行的概念到罪行理论的形成,《圣经》、《古
兰经》和《摩西五经》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虽然罪与恶(违背道德法
则)皆被视作不可接受的行为,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罪通常是对成文法
的违反。随着处罚罪行的责任从神学权威转移至国家,神职人员被警察
取代,“恶似乎消失了,因为它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和新的监控手
段”。[2]
“何为罪?”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通常的观点是将罪与恶,或
将罪与如今人们所说的反社会行为画上等号。但出于本书的写作目的及
结构连贯性考虑,我们在此将把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即是否违背法
律。读者会发现,一个社会的刑法主要着眼于该社会及其统治者的核心价值、道德和原则。事实上,在有些文化中,最初的文字记录或文学作
品正是以行为准则和法典的形式流传至今,且往往伴随着一系列惩罚条
款。将行为定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对罪行种类或个人罪行与国家暴
力的区分只有在相对成熟的社会中才适用,这一点已成共识。在史前社
会,罪犯由该地区的公众进行审判和惩罚,因为人们认为,罪犯的行为
危害了整个地区。放眼全球,社会与社会间千差万别,各个社会所定义
的罪行大相径庭,迄今犹是。本书基于过去20年对犯罪与惩罚史的关
注,薄薄一册,只不过是就该论题进行了跨越千年的综述,绝非综合性
的参考大全。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初期阶段的犯罪与惩罚状况,我们只能凭借假
想。人们已尝试在某些学科中通过对殖民时代前的传统文化的观察来进
行推断,并基于这些推断进行假设,从而解释晦暗不明的过往,弥合认
识的断层。在14世纪之前的英国,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谋杀和个人犯罪
的记录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认为,直到12世纪英国巡回法庭出现,国王
的法官才会定期在郡与郡之间巡视、记录犯罪活动的细节,对杀人罪和
其他罪行的系统研究方得以开展。[3]
随着书面资料的积累,罪与罚的历
史也自然变得更易梳理。之后,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不是单纯地收集点
滴素材,而是要对材料进行扬弃。
社会往往依照其文化信仰来设计惩罚的手段。例如,亚洲社会曾青
睐“其辱尤甚于死”的公开惩罚。没有哪种形式的死亡比死后还要被分尸
更可怕。人们相信,躯体完好无缺地入土为安,灵魂才能顺利升天,因
此斩首(通常还伴随其他形式的肢体破坏)便被视作极端的惩罚手段。
与媒体哗众取宠的报道以及流行文化对连环杀手、杀人狂的渲染相
反,长期的证据表明,我们的世界事实上正变得更加安全。[4]
自文明伊
始,人类似乎就展现出相互伤害的倾向,并发明了各种新奇手段来惩罚
那些违反社会行为标准的人。每种文化都形成了其对犯罪与惩罚的理
解。千年来,人们对恶行的反应惊人的一致,所不同的仅是受到技术与想象力的制约。早在成文法创立之前,人类社会就已有了规矩和习俗,以便维持秩序,形成约束,使社会免受犯罪者危害。研究者对这一时期
的称呼各有不同,但都尽力避免使用“原始”之类带有贬义色彩的词语。
学者在精神上更加中立,也不那么武断,他们更喜欢用更得体的词语,比如“史前的”“部落的”“无文字社会的”“前殖民时期的”等等。随后的关
键所在就是考察各个社会如何定罪并制定相应的惩罚。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对罪与罚的态度变化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棱镜,它折射出人类的进
步。
罪与罚的历史不断发展,新的发现总是不断打破业已被认可的观
点。想象一下,在1901年《汉穆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被
发现之前,我们对巴比伦法律的理解,或者想象一下在1799年之前、为
解开埃及象形文字之谜带来巨大突破的罗塞达碑(Rosetta Stone)尚未
被发现之前的埃及学。书写任何一种“全球史”都必须考虑到,大部分人
类活动根本没有书面记载。即便在21世纪,从人口稠密的地区获取有价
值的罪与罚的数据也绝非易事。因此,从诸如中国、越南、朝鲜、沙特
阿拉伯、苏丹和古巴等国收集有价值的犯罪数据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得
考虑从前文字时代追寻原始记录、建立历史档案所要面临的挑战。当你
对不透明的社会或专制政体下的罪与罚进行考量时,今昔有时也变成了
如往昔那般的“陌生国度”,成了令人沮丧的密码。因此,在涉及大时间
跨度的全球编年史时,无论何种题材,研究者往往都不得不借助推断、演绎和猜测。不过,我们也可以求助于民间传说、口述历史、传闻逸
事、神话和古典文学,以及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它们有时能带来意
外收获,以填补历史和史前记录的空缺。
当人们提起监狱和罚金、绞刑架和断头台、砍头或鞭刑时,指的无
疑是各种各样的惩罚手段。然而,说到犯罪本身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同
样的行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未必都会被视作犯罪。众所周知,宗教国家严
禁通奸、淫乱、亵渎神明、滥引主名、叛教和其他犯罪行为。但如果绝
大多数世俗国家并不禁止上述行为,对于通奸在美国24个州仍是一种犯罪,这一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呢?
关于全球犯罪与惩罚的许多基本理论并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例
如,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罪犯的惩处渐渐从体罚向经济补偿和监禁转
变。但纵观历史资料,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事实最为普遍,即受害者和犯
罪者的地位是确定判决结果与量刑的主要因素。从远古时代到封建时
代,再到如今,当人们需要同司法体系打交道时,特权阶层的身份总是
有利的。自第一部成文法典起,法律就已为富人所独享。《汉穆拉比法
典》明确规定,对低等阶层的惩罚最为严厉,律法之下完全没有平等可
言。在印度的大多数普通犯罪事件中,如果受害者是平民或低种姓人,那么富有的罪犯将受较轻的刑罚,支付较少的罚金。依社会地位定刑的
做法可以从印度古老的《摩奴法典》(Laws of Manu)、菲律宾的伊富
高人(Ifugao)以及中国的唐朝找到踪迹。不过,总是不乏奇怪的例
外,比方说,阿兹特克人认为贵族理应品行更端,因此倘若贵族违法,就会受到比平民更严厉的惩罚。此外,还有一些经久不变之处,比方
说,数世纪以来,罪犯,尤其是暴力犯,绝大多数是年轻男性。与此相
应,最残酷的惩罚也落在了男性的头上。例如,在英国历史上,从没有
女性被处以绞刑。
纵观史料,罪与罚发展中的另一种模式是对更人道的处决方式的不
懈寻求。从雅典人使用的毒芹和斩首,到断头台、电椅和毒气室的技术
奇迹,最后(截至目前)是注射死刑,刑罚改革者在决定如何处决我们
之中的败类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现代社会甚至还给一些如今仍在
使用的原始惩罚方式添加了新意。以往,罪犯在见刽子手之前并没有什
么准备,但在现代化的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死刑犯常常在被送往公共广
场斩首前注射镇静剂。在伊斯兰国家,那些面临削手削足刑罚的人也会
事先被注射适量麻醉剂。
采用全球视角的历史性叙事方式,不仅是要论证某些犯罪与惩罚的
普遍性,也是要试图让读者意识到,原始的惩罚手段并不比现代方式残酷。的确,刑罚是残酷无情、疏而不漏的,但总体而言,比起仅仅几个
世纪前还在西方使用的轮刑、火刑或开膛破肚,古代部落的刑罚要温和
得多。
所有历史作品,尤其是那些试图采用全球化视角的作品,都受制于
内容与长度、内涵与外延,本书亦不例外。我在此类或彼类罪行、此类
或彼类刑罚中反复斟酌,孰取孰舍取决于该类罪行是否与专门的成文法
相对应。固然,全球史可以涉及诸如战俘营与集中营、种族灭绝、恐怖
主义、宗教战争、种族和政治团体、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其他反异端宗
教运动等论题,但上述内容都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围。
涉及犯罪与惩罚的史料里不常出现儿童和女性。正如上文提及的,大多数罪行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年轻男性所犯。至于女性犯罪,我们会发
现,越向久远回溯,她们就越频繁地出现在巫术、通奸和杀婴之类“特
定性别”的案件中。由于儿童在司法体系中没有主体地位,提及他们的
史料便更少。本书下文对罪与罚的讨论着眼于不同文化中最具时间连续
性的部分。例如,虽然有若干书籍对绑架专门进行了探讨,但此类罪行
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不过,就全球犯罪与惩罚史而言,犯罪行为的
理论基础这一论题却是相当新的。例如,直到1874年查理·罗斯案
(Charley Ross case)之前,绑架在美国尚未成为“成熟的公共话
题”。[5]
另一个值得花整本书的笔墨进行探讨的问题是金融犯罪史。作为21
世纪(截至目前)的标志性犯罪,经济犯罪自第一批铸币诞生、第一次
税收令颁布、第一次金融犯罪行为出现以来便与我们如影随形。在大部
分历史文献中,金融犯罪指涉的是伪造货币、走私、逃税、行贿受贿等
等。但如今,当人们谈到这个话题时,主要想到的却是伯纳德·L.麦道夫
(Bernard L.Mado)案那种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诈骗案。新技术为行骗者
提供了难以置信的便利手段。自从17世纪商业迅速扩张以来,骗子横行
的状况已司空见惯,但彼时的骗子尚不足以成为危害全人类的毒瘤,因此也不在本书的讨论之列。
为了给犯罪与惩罚这对不可分割的话题组织起既广泛又有趣的素
材,作者深入挖掘了各国史学中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以往相关的书籍
主要以西方为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关于西方社会的原始素材更
多。本书试图拓展该研究领域,关注那些不为人所熟知、较少被载入史
册,因而其罪与罚的状况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历史性讨论的地方。为了达
到这个目标,我选取了大量富于启发性的话题、事件和故事,以便提供
某种时间上的推动力和连贯性。
第一章带领读者领略从史前到古代社会的刑法和惩罚。在陪审团、监狱和法庭系统出现之前,相比成文法,前文字社会的文化更依赖于不
成文的习俗。在对近东地区、埃及、印度、中国和其他地区最早的成文
法典进行探索之前,本章将先考察我们对这些文化已有的认知。
第二章考察了各种有影响力的法律传统的发展。回溯史料,诸多法
律传统起落兴衰,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四种法律传统。至今有的法律体系
依旧存在,比如伊斯兰法律传统、普通法传统、民法传统和社会主义法
律传统,而更多的法律传统则或消失或融入某种混合体系。由于欧洲殖
民势力在征服和统治的过程中,将普通法传统和民法传统传遍全球,所
以本章将重点关注这二者。
第三章考察了罪与罚在不同社会进入国家体制进程中的发展。本章
论述了在集权官僚体制兴起和威权建立之前封建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
为了征税、制定法律、保持和平所进行的司法实践。封建社会在日本和
西欧这两个迥然有别的地区都昌盛一时,直到19世纪,该体制依旧是维
系社会的重要力量。
第四章论述了惩罚的转型和现代监禁制度的发展。这个话题至关重
要,因为一个国家的惩罚方式可以向我们展现出一个国家的面貌及其文
明化程度。虽然各国对监禁的采用情况不尽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抛弃公开死刑和体罚,转而使用监禁作为惩罚手段。
第五章阐述了在犯罪全球化之前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直到19世纪,犯罪主要还是地区性行为。早期犯罪团伙往往出现在政府孱弱、警察无
能、民众分化的地方。几乎在每个国家里,各类非法团伙都惊人地层出
不穷。有些最早的记录来自亚洲,如13世纪日本带有幕府色彩的恶党
或“恶帮”。从印度土匪、苏格兰强盗到墨西哥银帮、巴西游击队,以及
其他各种各样的“亡命徒”形象,人们对亡命徒的印象可谓五花八门。欧
洲甚至还有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盗贼。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只活跃于
能得到某些民众支持的地区,通常是在乡村。此外,一旦政府的组织更
有效或警力更充足,他们便好景不长。直到组织更严密的犯罪团伙——
奴隶贩子、海盗和贩毒集团——的兴起,同时伴随着运输、通信手段的
进步以及因全球各地不同禁令而产生的机会,犯罪活动才开始超越国
界。
第六章在前一章聚焦地区性有组织犯罪行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追
寻了国际犯罪团伙的根源。全球化发展促进了交通运输的改善和通信的
进步,加之一些考虑不周的商业禁令的通过,刺激了跨国犯罪团伙的兴
起,并令其得以继续危害现代社会。
第七章探究了谋杀的历史,重点关注多重谋杀和与性相关的谋杀形
式。诚然,本章也可着眼于抢劫、强奸、贿赂和其他活跃了数个世纪的
种种罪行,但没有哪种罪行能比始终被人们大书特书的谋杀更具代表
性。从古希腊文学和《圣经》,到莎士比亚的作品,再到当下流行的犯
罪纪实文学,谋杀一直是世界文学界的热门主题。尽管我们人类在科学
和文化上取得了进步,但我们仍然以惊人的速度自相残杀。据估计,20
世纪,有100多万名美国人被谋杀(不包括战争中的受害者)。人类历
史有多久远,谋杀的历史就有多久远。一个多世纪以前,弗雷德里克·
威廉·梅特兰(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曾说:“如果一个仙女给他机
会,让他亲自见证各个社会中的同样类型的场景,他会选择谋杀审判,因为它揭示了首要之事的方方面面。”[6]
一名犯罪历史学家甚至认
为,“谋杀”这个词在日常用语中最为重要。与亵渎神明、过失杀人、弑
君和恋童癖等罪行不同,当提到“谋杀”这个词的时候,任何人都明白那
指的是夺人性命。正如历史学家罗杰·莱恩(Roger Lane)所言:“事实
上,谋杀是最容易深究其历史的一种罪行:总是受到认真对待,总是有
法可依,且从未变得稀松平常以至于被人们容忍或忽视。”[7]
被研究最
多的一类谋杀大约是连环谋杀。在大众的观念中,连环谋杀是一种现代
现象,但事实相反,有证据表明,连环杀手自古有之。只要看看童话故
事、魔法故事和数世纪以来关于狼人和吸血鬼的记载,就可略知一二。
从非洲到西欧,各式各样豹人、狼人之类的故事很可能是从现代警察和
法医调查尚不存在的迷信时代的真实分尸凶杀案中得到了灵感。
第八章探讨了殖民主义和其他政权的建立过程在惩罚的全球化传播
中所扮演的角色。彼此相邻的国家,其罪与罚的理念往往相似。在相对
孤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国家,比如中国和埃及,其罪与罚的观念则往往
有天壤之别。但就罪与罚的理念传播而言,最强有力的途径之一莫过于
欧洲殖民主义进程。数个世纪以来,世界强国在全球建立了殖民地,一
方面传播他们的刑罚理念,一方面吸收借鉴当地的传统。此后,当这些
殖民地、海外领地和受保护国纷纷独立建国,它们的许多刑罚理念都是
建立在本土和殖民时期惩罚实践的基础上的。
第九章是这段漫长罪与罚之旅的终点。本章展示了罪与罚的循环,以及古代和现代犯罪行为之间显著的连续性。在高科技犯罪日益发展和
增多的同时,诸如亵渎神明、信奉异端邪说、通奸、海盗和巫术等古老
的罪行依旧长盛不衰,处决、耻刑、流放等古老的刑罚也相伴而存。此
外,本章也指出,当涉及犯罪与惩罚时,一个社会往往会求助于历史资
料,从过往的犯罪控制经验中寻找策略,同时对先前严重依赖死刑和监
禁的惩罚制度提出质疑。
罪与罚的全球史表明,尽管人类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辉煌的进步,但人们实施的犯罪行为以及对该行为的相应惩罚有着明显的延续
性。在数字化的后工业时代,虽然犯罪手段日新月异,但犯罪目的和动
机以及审判体系与早先的差异并不大。归根结底,本书表明,罪与罚的
历史乃是一部反复无常的实践史——借鉴、吸收、寻找新的替代品,司
刑者往往回到故纸堆中,向当前的新世界重新祭出古老的惩罚手段。虽
然关于上述现象的证据并不充足,但在过去几十年间,人们的确看到,行耻刑、用锁链将罪犯锁在一起,以及公开行刑等旧式处罚方式已死灰
复燃。
[1]Itamar Eichner,‘Israelis Enjoying Life in Swedish Prison’,www.ynetnews.com,12June2006.
[2]Karl Menninger,MD,Whatever Became of Sin?(New York,1973),p.50.
[3]James Buchanan Given,Society and Homicide in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Stanford,CA,1977).
[4]参见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trans.E.Jephcott(Oxford,1978);Steven Pinker,The
Better Angles of Our Nature: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New York,2011);Manuel Eisner,‘Long-term
Historical Trends in Violent Crime’,Crime and Justice:A Review of Research,xxx(2003),pp.83~142。
[5]Paula S.Fass,Kidnapped:Child Abduction in America(New York,1997),p.10.“绑架”这个说法
源自“窃贼”一词,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该词是由“孩子”(kid)和“攫取”(nap)组合
而成。
[6]Pieter Spierenburg,A History of Murder:Personal Violence in Europ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Cambridge,2010),p.1.
[7]Roger Lane,Murder in America:A History(Columbus,OH,1997),pp.1~5.第一章 罪与罚:太初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于北欧泥炭沼泽的防腐特性,铁器时代早
期那些令人惊骇的男性、女性和孩童的尸骨几乎完好无损地展现在世人
面前。这些尸骨有的还保留着被扔进沼泽前受处决的痕迹,比如割喉、勒痕、骨折和其他创伤,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公元前350年的林多人
(Lindow Man)古尸,它于1984年在柴郡(Cheshire)的一处沼泽中被
发现,目前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里。现代技术手段让科学家得以还原他
生前的最后时刻,并鉴定尸体上的无数伤痕以及依旧紧紧捆绑着四肢的
绳子,而这些折磨仅仅是他被割喉的前奏。尸体脸部和颅骨上的多处伤
痕表明,他是被杀死后弃尸于水中的。还有些尸骨带有被绞死、勒死和
斩首的印记,这使得考古学家推测,这些象征着“审判与惩罚意识初露
端倪”——至少在北欧是如此。[1]
无论如何,由于无法判断是被谋杀还
是被处决的,林多人之死的真实场景将永远是个谜。[2]
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写于公元1世纪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北
欧前文字社会惩罚实践的最早记录。塔西佗称,沼泽处死(他把沼泽中
的尸体称为corpores infames,或臭尸)是对诸如通奸等各种性犯罪的惩
处,而且:
具体的处罚方式依罪行而异。叛徒和逃兵被吊死在树上;懦夫、逃
兵和鸡奸者被塞进藤条笼里浸入泥泞的沼泽中。惩罚手段的区别是基于
这样的理念:背叛国家的人应当被拿来杀鸡儆猴,而做出不齿行为的人
则应从公众的眼前消失。
但此处的关键词依旧是“可能”,因为尽管有这些我们自认为已掌握
的关于前文字时期的知识和古代历史学家的叙述,在沼泽尸骨究竟是惩罚、祭祀神灵的结果,抑或二者皆是的问题上,我们仍未能达成共
识。[3]
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并不是自然死亡。
自古以来,人类似乎就已经有了制造骚乱并对制造骚乱者实施千奇
百怪的惩罚手段的本能。事实上,暴力和同情似乎常常在我们体内共
存。关于此类行为的最早书面证据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古代中东地
区。不过,人类的历史要比那久远得多。
某些秩序理念在各种文明中都发挥了稳固作用,比如我们不可否
认,为了更广泛的社会的利益,个体的冲动必须以某种形式加以约束。
各路权威声称,法律只存在于有法庭体系且法律条文能得到政治组织结
构化的国家支持的地方;但前国家时期的文明极少拥有这种意义上的法
律。然而,保护社会成员免受他人恶意伤害的规则却比比皆是。就此意
义而言,大多数前文字时代中的确存在法律。不过,这些法律之间有着
天壤之别。早期人类社会形态各异,其习俗和信仰体系也千差万别。正
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言:“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远古法律’,一如不存
在天下大同的原始社会。”[4]
尽管如此,每个文明都为管理和规范行为
制定了规则。
在文字出现之前,当时的人们将我们所谓的“罪行”或“恶行”与那些
极有可能令诸神迁怒于族群的行为——那些被认为有害于整个社群的行
为——等同视之。例如,在非洲阿善提部落的人眼中,罪即是恶,指的
是“令族人厌恶”或不仅冒犯部落祖先神灵,也极有可能为整个部族招来
神明之怒的行为。因此,部落首领要惩戒作恶者,否则族人将遭受祖先
怒火的惩罚。[5]
我们已有的或自认为已有的关于前文字时代罪与罚的知识,大多是
基于推测,基于人类学、人种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但没有书面记录,任
何发现都不尽准确,只能纯然仰赖口述历史和对现存游牧和狩猎采集者
群体的观察。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萨瑟兰·拉特雷(Robert SutherlandRattray)在20世纪初研究非洲阿善提社会时,认为那些人是“和平的”,在他们中见不到任何积怨仇杀的痕迹,部族的惩罚体系掌握在法官、酋
长和国王等高级领导者手中。他颇为自信地推测,地位越高的阿善提人
受到的惩罚越严厉,这“可能与早期正义背道而驰”[6]。“可能”一词在此
不可或缺,因为没有记录的历史只不过是一种有根据的猜想。拉特雷对
过往的诠释至多不过是考察了欧洲人到达之前的阿善提文明。他最惊人
的断言之一是,最严厉的制裁似乎是“嘲笑的力量”。通观他的研究以及
对口述传统的考察,他发现人们对嘲笑的恐惧始终存在,也就是
说,“与这种笑里藏刀、剥夺了一个人的自尊和被周围人尊重的武器相
比,即便最残酷的惩罚也未必更可怕”。阿善提人有句谚语:“若要在耻
辱与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则宁可选择死亡。”这种信念在一则小故事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一名乡村长者向来访的显要人物躬身致敬,却“无意
间放了一个屁”。不到一小时,长者回到家中悬梁自尽。当有人怀疑此
长者的极端反应乃是由于精神错乱时,他的部落兄弟们却一致认为他在
这种情况下做了恰当的事。[7]
由于口述传统以及由人种学家和人类学家,如拉特雷所做的研究,我们有了一些阐释早期阿善提人罪与罚传统的基础。最常见的死刑行刑
方式是用小刀斩首。行刑者要抓住受刑者,从脖颈处由前向后切割。但
行刑者“若不愿直面受刑者的脸”,务实的阿善提传统也允许行刑者按住
受刑者的头部,“从脖颈后方切割”。其他方式包括用皮绳或徒手扼死,以及用大头棒打死。[8]
此外,某些残肢手段也可以作为处罚。若受刑人
被认为犯了不敬之罪,可能会被割掉整只(或部分)右耳。有一则广为
流传的故事可为我们提供佐证。故事中说,一名男子被判用一只绵羊作
为对冒犯他人行为的赔偿,该男子却回答说,用一头牛更合适,尽管他
很清楚牛这种动物不为本族群所容。结果,他被割掉了双耳。在其他情
况下,那些被控做伪证或出口伤人的人会被割掉嘴唇;割鼻适用于对傲
慢无礼或自我夸耀、飞扬跋扈者的惩罚。[9]
宫刑是专门用于惩罚那些不
经意间窥见了首领的裸妻的宫廷侍者,因此,侍者往往要在进入宫闱时高呼“嗖嚯,嗖嚯”,以宣告自己的到来。当然,还有其他种种刑罚,但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直到欧洲人到来之前,在除谋杀罪之外的特定情况
下,当地人可以通过“买人头”(支付罚金)的方式免于被处决。被判死
刑的孕妇会被拴在木桩上等待分娩,之后,母亲和婴儿都会被处死。后
来,在阿善提建立殖民地的英国人也允许被判刑的女囚在被处决前分
娩,以此彰显其文明。二者相比,唯一不同的是,后一种情况下出生的
孩子会被收养。
说到罪与罚,几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范。实际上,“似乎并
不存在绝对一致的人类良知”,至少,历史学家雅克·巴赞(Jacques
Barzun)是这么认为的。[10]
不过,乱伦似乎在全世界都被视作不可容
忍的犯罪行为。在史前社会中,血缘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牢不可破的纽
带,这意味着早在史前时代之初,乱伦的禁忌便存在于几乎所有文明
中。乱伦属于要被判死刑的性案。阿善提人认为乱伦的行为罪可处死,并视之为mogyadie,即“饮自己的血”。但是,他们所谓的乱伦,其含义
较之现代意义要宽泛得多,它囊括了与任何属于同一血缘或氏族的人发
生性关系,无论两人的关系亲疏,只要他们的姓氏相同,就足以被双双
处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最为人所唾弃的恶行。
至于通奸,尽管往往仅在女性为过错方时才会进行惩处,却并不像
乱伦那样具有普世规则。最早的成文法对通奸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汉穆拉比法典》、《希伯来法典》和后来的古希腊法典均规定,犯通
奸罪的女性将被处死。值得指出的是,在汉穆拉比统治时期(约前1792
年—前1750年),巴比伦的居民可能实行某种形式的祖先崇拜,而通奸
行为会危害或削弱血统,因而被视为亵渎之罪。在现今留存的近东地区
最早的关于通奸的法律中,规定了旨在约束家庭成员关系的残酷惩罚。
在通奸问题上,丈夫可以决定是处死妻子及其情夫还是将他们双双致
残。如果是后者,则妻子可能会被割鼻,其情人会被阉割和毁容。在今
天的喀麦隆,图普里部落的通奸妇女必须终生佩戴铜圈;在美洲原住民
黑脚人中,若妇女通奸被丈夫当场抓获,就不得不立刻接受割鼻的惩罚。
在一些部落文化中,各类杀人行为,无论是事出偶然还是蓄意为
之,因令统治者失去了臣民,故均被视作犯罪。[11]
与西方法律不同,乌干达塞贝人的法律规定,杀害近亲不算谋杀。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
必须意识到,在此,家族是个法律实体,且他们尊重杀戮。在这种情况
下,家族首领会表现得相当务实。一名研究过塞贝人的人类学家记得这
样一个案例:家族首领认为,“一个生命已经被毁灭了,我们不能让家
族一下子失去两个人。死者是坏人,死有余辜”。一些非洲部落社会,比如非洲西南部的班图部落,对过失杀人和意外伤害做出了区分;而菲
律宾的伊富高部落则对故意、过失和意外行为做出了严格区分。在一些
美洲原住民平原文化中,对杀人的惩罚是四年的流放。在此期间,杀人
凶手被要求留在营地周围,并不得与除直系亲属外的任何人接触,而他
的直系亲属则被获准为他提供食物。惩罚期的长短取决于受害者亲属的
态度,因为只要他们同意,杀人凶手就可结束流放。[12]
波尼人部落很
少以命偿命,而居住在弗吉尼亚州的波瓦坦部落(Powhatan
Confederacy)则把杀人视为对部落的冒犯,要求以酋长的名义处决触犯
者。荣誉杀戮、仇杀、赔偿和赎罪金
为荣誉之故而实施的犯罪如今在世界很多地方依旧常见。但若论此
传统的传承,没有哪里能比地中海地区更强。早在公元前400年,该地
区的丈夫就可以合法地杀死有通奸行为的妻子(以及情人)。时光飞逝
2400年,到了20世纪,意大利刑法第587条规定,若被戴绿帽子的丈夫
(或愤怒的父亲、兄弟)杀了出轨的妻子(或女儿、姐妹)或她的情
人,只需在狱中服刑3~7年。与此类似,黎巴嫩刑法第562条允许男性杀
死因性行为“给家族蒙羞”的女性亲属。20世纪70年代,一个妇女团体试
图推翻这条规定,但身为基督徒的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Suleiman
Frangieh)回应说:“不要触碰荣誉。”作为对这句话的行动响应,他在
一名男子勒死其与人调情的女儿仅仅9个月之后便赦免了该男子。直到
20世纪,维护荣誉这个理由仍在美国至少3个州得到认可,包括得克萨
斯州。仅在20世纪80年代,巴西圣保罗就有722名男子使用了维护荣誉
这个理由,直到1991年该理由被取缔。值得一提的是,在拉丁美洲,为
维护荣誉而犯罪的理念只是几个世纪前众多输入新大陆的殖民文化观念
之一。
人类在早期社会就已意识到通过禁止氏族宿仇升级来维护秩序的重
要性。其中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规定只有由受害方家庭的一名成
员对侵害人本人实施的杀戮或残肢行为才是被许可的复仇,且复仇行动
应止于此。至此,侵害者的家庭与仇杀不再相干,并已向受害者家庭偿
清了债务。早期法律体系中最常见的理念之一是用赎罪金或赔偿代替复
仇。《汉穆拉比法典》和其他美索不达米亚法律以及《旧约》(尤其是
《出埃及记》和《申命记》)都包含了赔偿条款(后来的伊斯兰律法亦
然)。赎罪金在日耳曼法律中同样极为常见,且男系亲属负有偿付责
任。赔偿制度在盎格鲁-撒克逊司法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约1500
年前的《埃塞尔伯特法典》(Laws of Ethelbert)中罗列了对各类伤害的具体赔偿细则。
赎罪金在伊斯兰律法中由来已久(见第二章)。即便是在今日的巴
基斯坦,因杀戮引发的纷争也依旧可以通过受害者的继承人与侵害者之
间达成赔偿协议的方式实现庭外调解。前者必须宽恕,后者必须支付赔
偿。中央情报局(CIA)探员雷蒙德·戴维斯(Raymond Davis)经历的
一起案件足以说明这一点。戴维斯称自己杀死两名巴基斯坦人是出于自
卫需要,但仍旧遭到了逮捕。巴基斯坦的高级官员表示,可以通过向死
者家属支付赎金的方式了结此案。[13]
几个世纪以来,即便在那些家族仇恨可以逾越法律而得到认可的地
方,往往也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直到20世纪,阿尔巴尼亚的刺客仍应
在行刺之前警示受害人,且永远不得从背后下手。一旦刺杀成功,要将
尸体以仰卧姿态放置,且任何人不得劫掠尸体。另一些规定禁止在市场
或繁忙的道路上袭击牧羊人或实施谋杀。在阿尔巴尼亚,当家族仇恨涉
及的任何一方想种田、举行聚会或做生意时,可以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暂时搁置复仇。死者家属被允许在凶杀发生的24小时内向凶手或其任何
亲属寻仇,24小时之后则只能对凶手本人实施报复。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大量证据表明,很多文明都认可用某种形式的
物质补偿来避免愤怒的受害人家属或亲族实施报复。但亦有大量资料表
明,各个文明对于何种罪行可以用赔偿方式解决意见不一。例如,伊富
高人的习惯法(来自菲律宾吕宋岛)允许除故意杀人罪之外的几乎所有
罪行适用赔偿代责,对故意杀人罪则必须血债血偿。
在其他承认集体责任的文化(意味着犯罪者的亲族也有责任)中,某个家族成员被杀会引发家族世仇。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的原住民采
用“合法对抗”的方式来避免上述情况。“合法对抗”的一方是持盾的罪
犯,另一方是被害人的亲属或近邻。被害人的亲朋好友可以向凶手投掷
长矛,凶手则全力躲避。一旦凶手受伤流血,无论是死是活,对抗(以及双方未来的冲突)即宣告结束。与后来那种用折磨手段判定有罪或无
辜的审判不同,这里提到的凶手首先须是已确定有罪之人。
在另一些文明中,比如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对于伤害、偷盗、毁
坏财物或用不齿手段诱拐他人妻子的事件,会编出讽刺歌曲来嘲笑犯罪
者,“夸张地嘲弄他们,甚至抖搂出对方的陈年家丑”。受嘲弄的人可以
用同样方法做出回应,但最关键的是没有明显的肢体冲突。不过,如果
涉及凶杀,罪犯的麻烦就大了,因为受害人的近亲可以用相似的手段报
复加害者或其近亲。集体责任的观念有可能在无意间将仇恨传给下一
代,导致众多无辜生命的逝去。如一位人类学家所述:“在人们试图惩
罚凶手之前,罪行或许已过去很多年,而在此期间,凶手或许曾拜访受
害者的近亲,受到他们的欢迎和款待,平静地生活了很久。然后,他可
能会突然被同伴派去参加狩猎活动或摔跤比赛,且如果不能取胜就要被
处死。”[14]
某些南非部落,比如祖鲁族(Zulu)和科萨族(Xhosa),让我们
看到了部落刑法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公正掌握在部族首领手中,因为按
照传统,所有族人都属于他。因此,他也要对受害人的一切损失做出补
偿。一名男性值7头牛,一名女性值10头牛(差别在于女性出嫁时可以
获得的彩礼)。1820年之前,丈夫可以杀死奸夫且免受惩处。在大多数
情况下,对罪行的处罚以罚金为主。
从古到今,复仇一直是惩罚体系背后的驱动力。近年来发生在拉丁
美洲、中东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案件一次又一次表明,农业社会的人倾向
于以正义的名义自行执法。2003年6月11日,墨西哥拉坎德拉里亚村
(La Candelaria)的村长在遭绑架和谋杀后被埋葬。村民迅速围捕了四
名嫌疑人,用私刑处死了其中两人,听任另外两人慢慢等死。被制度腐
败和镇压激怒的当地居民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行使了超越法律的公
正,这让一名观察者认为“恰帕斯(Chiapas)从来不存在法律制度”,并
说“当人们无法获得公正时,就处在一个全然不同的境况中,[且]公正由那些实施公正的人来定义”。2002年,早在如今的贩毒集团火拼之
前,私刑在墨西哥不少原住民居住的地区相当常见。很多杀戮都是由家
族仇恨和世仇所致。警方则认为“印第安人杀印第安人不足为奇”,不愿
介入,以免“打破村庄内部以及村与村之间脆弱的力量平衡,而这种力
量平衡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该地区的秩序”。[15]
时隔两年,玻利维亚的一名镇长被粗暴地吊在灯柱上焚烧。当绳子
系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已经被殴打致死。当地居民在实施此次私刑处
决前曾经历了一场并不成功的法律诉讼。他们向玻利维亚财政部、参议
院和法庭控诉有人侵吞了本应用于贫苦村民的数十万美元政府资金,但
均以败诉告终。饱受欺压的阿尤阿尤村(Ayo Ayo)的镇长之死被人们
普遍视为“群体正义行为”,这种行为在拉巴斯(La Paz)以南一小时车
程的小山地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正如一名观察者指出,镇长被
杀“是因为他是令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贫苦无助的不公正制度的一部分”。
用一名农民的话说,那些统治国家的白人和混血儿精英“也该落得同样
下场,如果不被烧死,就该被淹死、绞死或者四马分尸”。这个观点受
到了一名社会学家的支持,他将私刑处死看成是“对普遍视作服务于富
人和权贵利益的司法体系的拒斥”。无论如何,这种死亡惩罚只有在整
个社群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极端情况下才会被使用。[16]《汉穆拉比法典》
1901年,法国考古学家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发掘
出《汉穆拉比法典》,这是一块8英尺[17]
高的黑色玄武岩石板,上面刻
有4000行楔形文字。[18]
此地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环境
宜居,早在约5000年前就已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组织。这部法典后来进一
步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的刑罚程序,但其法条只在与近东地区接触后才
会影响古希腊和古罗马。
大量证据表明,新月沃地较早的法典在汉穆拉比之前约300年就形
成了罚款和赔偿制度,可追溯到第三乌尔王朝的建立者乌尔纳姆(Ur-
Nammu,约前2111年—前2095年在位);那部法典中的部分措辞也被
挪用到了《汉穆拉比法典》中。不过,令《汉穆拉比法典》卓然于世的
是,它首次提出了“以眼还眼”的原则。与早前依靠罚款和各种补偿手段
的法典不同,《汉穆拉比法典》引入了复仇的概念,被认为是第一次试
图控制私人复仇行为。这部复仇之法从字面上看是一种问责制。比方
说,如果一座房屋倒塌并导致屋主的儿子死亡,要偿命的不是造屋者,而是造屋者的儿子。不过,如果在房屋倒塌事故中丧生的是一名奴隶,造屋者只需向受损者赔偿另一名奴隶即可。另一则条款规定,“如果一
名男子攻击了一名女性自由民并导致她流产,则该男子应赔偿她10谢克
尔的损失”。但如果该女性死亡,则行凶者的女儿就会被处死。与此类
似,趁火打劫的人会被投入火中。这些法律的影响力在近东地区的历史
上显而易见。1903年的考古挖掘中发现的年代稍晚的、刻在一系列陶土
碑上的亚述法典用楔形文字重申着同样的理念:“如果有女性在与男性
市民的打斗中打碎了后者的一个睾丸,则要被判截去一根手指,如果经
过治疗,另一个睾丸也破碎了,则要被判弄瞎双眼。”直到1999年,巴
基斯坦法律仍规定,被害身亡者的家庭成员可以用该凶手作案的手法杀死已被定罪的凶手(也可以慈悲为怀)。一个用扼杀、肢解、溶尸的手
段杀害了100名儿童的连环杀手被判以同样的方式处决,便是很好的证
明。
大体而言,《汉穆拉比法典》共有282条,每一条都体现了国王的
一项革新。法典不是一套完整的法律,而是设立了分别针对巴比伦社会
三个等级民众的一系列惩罚措施。但它的缺憾在于,它没有编纂新的法
律体系,既不指导法律程序,也不告知公民的权利与义务。[19]
法典规定的惩罚是严酷的,但相比距今短短几个世纪前欧洲使用的
轮刑、烹刑或开膛破肚则温和得多。《汉穆拉比法典》里约有30次提及
死刑,非死刑类的身体惩罚包括割舌、剜眼、削胸和鞭笞。溺死之刑用
于通奸犯、与儿媳乱伦者,以及在酒馆里以水掺酒欺骗顾客的人。木桩
穿刺刑是对强迫他人堕胎的女性的惩罚。
汉穆拉比声称自己是该法典的作者,法典的条款是国家权力的世俗
体现。国家对越轨行为的反应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复仇:以死偿死。复仇
的概念对大多数刑法体系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该法典也引入
了“具有表现力的”“刑同其害”的惩罚原则,对罪犯的部分身体实施体
罚,通常是断肢或某种形式的致残。例如,如果一个人偷了别人的东
西,他将要支付罚金或被砍掉一只手;若再次犯同样的罪行,则会被砍
掉另一只手。如果一个男人亲吻一个已婚女人,他将被割掉下唇。类似
地,猥亵案的罪犯会被砍掉手指,强奸犯会被阉割,而那些诽谤他人的
人会被割舌。
《汉穆拉比法典》或许也是第一部涉及经济犯罪的法典。法典中提
到了对窃贼的惩罚,但也适用于“酒馆招待”——通常是女性——的诈骗
行为。她们不“接受人们用谷物按重量支付酒资,而是要收钱,且酒的
价格低于谷物的价值”,从而触犯了法律。[20]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女
人“应被定罪且扔进水里”,即被溺死。地位、罪行与惩罚
在汉穆拉比时期的巴比伦,社会等级分化进一步加剧。因此,他的
法典成了富人的法律,明确规定侵害者和受害者的社会身份将决定适用
何种惩罚。对罪行的惩罚取决于受害人和罪犯分别属于三个等级中的哪
一个。例如:“如果贵族打断了另一名贵族的骨头,侵害者将被打断骨
头。如果贵族伤了一个平民的眼睛或打断了平民的骨头,他要为此赔付
一米那[21]
的银子。如果贵族伤了另一名贵族的奴隶的眼睛或打断了奴
隶的骨头,则要赔付该奴隶身价的一半。”这种分级惩罚体系取决于犯
罪行为的严重性和罪犯的社会身份。普通女性可以去酒铺,但如果女祭
司走进酒铺则会被判火刑。如果酒铺的女老板在分量上做手脚,会被投
入河中;但如果她允许强盗利用她的店铺接头,她会被处以死刑。
依照受害人和侵害人的地位决定惩罚的尺度,并非巴比伦独有。印
度的《摩奴法典》也是根据当事人的种姓等级来惩罚犯罪行为。高等级
的婆罗门通常只会被判处罚金或不受任何惩罚。他们即便杀了人,也至
多被判放逐。另一个极端是低等级种姓的首陀罗,他们即便犯了最轻微
的罪行也会受到体罚。根据《摩奴法典》:“首陀罗若扬起手或棍子,就要砍掉他的手;如果愤怒时用脚踢人,就要砍掉他的脚。”谋杀婆罗
门是死罪,低等级种姓的人攻击或诽谤高等级种姓的人则会受到“刑同
其害”的惩罚。例如,如果一个首陀罗伤害了一名婆罗门,该首陀罗在
攻击中使用的肢体就要被砍掉,向高等级种姓的人吐口水则会被割掉嘴
唇。类似地,如果他把尿撒在了高等级种姓的人身上,会被割掉阴
茎,“如果他冲高等级种姓的人放屁,就会被割掉肛
门”(Ⅷ:279~280,282~283)。他有诽谤行为,会被割掉舌头,对使用冒
犯的语言提及高等级种姓人的名字和种姓的行为,惩罚是把“十根手指
长的铁钉”和“烧红的钩子”塞进他的嘴里(Ⅷ:270~272)。在唐朝(618—907),中国人也依等级量刑。地位高的罪犯可能会
受到较轻的惩罚,或者完全免于惩罚;而犯了罪的仆人和家奴会受到较
常规惩罚重一等的惩罚,至于奴隶则要加重两等。比方说,如果一个奴
隶攻击平民,使其四肢或眼睛受伤,该奴隶会被处死;相反,如果主人
(无缘无故地)杀死自己的奴隶,至多会被判一年劳役。我们从不同的
资料中发现,在墨西哥早期的阿兹特克文明中,阿兹特克人同样依等级
量刑,但具体的方式略有不同。比如,若案件涉及公开酗酒、行为有失
身份的情况时,对贵族的惩罚比对平民的更严厉,但在通奸案中,贵族
受的惩罚较轻。[22]
直到20世纪,很多非洲国家仍沿用习俗规范进行判决和惩处。比如
在尼日利亚,一个人的身份往往决定着他要受的处罚。首领或富人不会
因杀人被处死,他们可以将奴隶作为对受害者家属的赔偿,或让奴隶代
替自己被处死。同样的案件,地位较高的人可以支付罚金,地位较低的
人则要被判奴役。[23]
20世纪的菲律宾伊富高人依旧认可贫富有别;社会地位不同,相应
的罚金也不同,这与《汉穆拉比法典》的规定大同小异。他们明文规
定,若犯杀人罪(无须血债血偿时),富有的罪犯要准备“丰盛的宴会
和各种物品分发给死者的继承人”,除非受害者是下等人。若受害者来
自中等或更低种姓的阶层,赔偿会少得多。然而,如果行凶者属于较低
的两个种姓,无力以“物质代偿”的方式支付罚金,则不仅他的余生要背
负这笔债务,甚至还要父债子偿。[24]摩西律法和近东地区的传统
《汉穆拉比法典》对希伯来律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
上,希伯来律法中的大量词汇均出自苏美尔和巴比伦的法律传统。例
如,现代正统犹太教徒使用苏美尔词语表述离婚,这表明希伯来词语
keritut(分离或中断)有可能源于古苏美尔人的做法:丈夫“割断妻子衣
袍的一角以象征割断婚姻纽带”。[25]
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当正统犹太
教徒在犹太教堂里诵读《摩西五经》时,仍然会用祈祷披肩的边缘触碰
卷轴上的相应地方。他们做得如此自然,并未意识到其实自己正重复着
一个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传统,即要求人们用外衣的绲边拂拭陶碑以表
示对法条的遵从。[26]
无论如何,包含了《十诫》的《圣经》前五卷,也就是希腊人所谓的《旧约》首五卷、犹太人所谓的《摩西五经》,为
西方世界大部分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
《圣经》中描述的传统家庭类似于一个以父亲为首的、拥有生死裁
量权的大家族。在古希伯来人的村落里,权力掌握在父辈们手中,他们
也是整个社群的首领,这体现了男性主导的司法体系。家庭中往往包括
若干对有生育能力的成年人和他们的子女,人数足以自我保护并自给自
足。当家庭中的一名子嗣或某个家庭成员被另一名家庭成员伤害时,将
由父亲决定赔偿的数额,而这个数额通常取决于在儿子受伤休养期
间“损失的工作量”(《出埃及记》,21︰18~19)。如果坚持要伤害行
凶者,则会令家庭损失两个劳动力,反倒事与愿违。如果受伤的是女
性,则赔偿取决于袭击行为对其日后生育能力造成的影响。在杀人案
中,如果凶手与受害人来自同一个家庭,即为手足相残;若凶手来自另
一个家庭,则被视为谋杀。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将遵循对等原则进行处
罚,一命偿一命。村民会议将决定是判凶手本人死刑,还是让其家中的
另一名成员顶替。另一方面,村名会议也有可能允许凶手的家庭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赔偿。是否适用死刑判决,需要从整个村庄的最大利益着
眼。如果会议认为不诉诸以命偿命的方式更有利于村庄,则可以适用赔
偿。[27]
随后,凶手要向受害者家属献出土地和子嗣。与希伯来人相
似,非洲的一些村落也用赔偿替代死刑,赔偿给受害者家庭的通常是牲
口、与受害者身体条件相仿的人,或可以为受害者的家庭生育子女的女
性。
虽然摩西律法并未跻身世上最伟大的法律体系之一,但它的《十
诫》或许是史上最著名的行为禁令;所不同的是,《十诫》没有包含对
每一种罪行的具体惩罚,因此不应被误认为是法典。希伯来律法讲求刑
同其害(受害者受到怎样的伤害就怎样惩罚凶手)。“以眼还眼,以命
偿命”这句谚语最好地诠释了他们的罪与罚。这种严格字面意义上的罪
与罚在《出埃及记》(21:23)里是这样写的:“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
打。”直到后《圣经》时代,评论家才开始用比喻手法诠释这些词,给
惩罚设置了诸如“至多一只眼”或“至多一颗牙”的限制。彼时的着眼点已
明显从身体伤害转到了某种形式的经济补偿上。
巴比伦律法和犹太律法有几个主要分歧。在古代以色列,涉及财产
的罪行从不会被判死刑,而是适用罚金。由于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人是根据上帝的样子造出来的,因此摩西法典在很多方面比早前近东地
区的律法宽容得多,它既尊重身体,也极力避免部落流血。相反,在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杀人案中,受害者可以接受经济赔偿;而根据犹太律
法,已定罪的凶手则会被处决。根据希伯来《圣经》,夺去人类的生
命,即杀人行为,只有在自卫、战争和适用死刑时才被允许。古代希伯
来人确定了36种当判死刑的罪行,包括杀人、某些性犯罪、偶像崇拜、亵渎神明、不守安息日和行巫术;上述种种日后都在西欧产生了影响,令成千上万名女巫在5至17世纪命丧黄泉。
非死刑罪行通过各种非致死的手段进行惩罚,包括监禁、放逐、罚款和刑同其害的惩罚等。对于非故意杀人或过失杀人,罪犯有可能被判
放逐到六个避难城市中的一个,但绝不会被放逐到非犹太人的土地上,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被迫崇拜异教神明。同样,在避难城市
中,罪犯会受到保护,以免遭受害者亲属的私刑。正如我们前面提到
的,刑同其害的惩罚会让罪犯承受与受害者相同的伤害。放逐一直持续
到该城的大祭司去世。被判放逐的罪犯自然希望刚刚到达流放地就有年
长的祭司去世,因为倘若大祭司年富力强,这放逐恐怕就成了终身监禁
了。在罪犯被迫住在避难城市期间,当地的大祭司家庭会为他们提供衣
物、住宿和食物。
《圣经》中提及了一系列处决方式,包括火刑、石刑和斩首,其中
最常见的是投石击毙,即石刑。这种刑罚的参与者包括整个社群成员,特别适用于被认为给整个社会带来最大威胁的那些罪犯。行刑时,提起
诉讼的证人要最先投掷石块,其目的在于杜绝不实控告。石刑是死刑惩
罚中最古老的一种。两千多年来,这种惩罚手段已经在许多国家使用。
最早规定该刑罚的是摩西律法,但由于伊斯兰国家在当代也偶尔使用,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它或许与后者的联系更密切。最近的两次石刑分
别于2007年和2010年发生在伊拉克库尔德雅兹迪(Kurdish Yazidi)社区
和阿富汗北部地区;在后一起事件中,一对年轻夫妇因谋划私奔而被石
刑处死。石刑往往遵循特定的程序,受刑的男性在行刑前要被埋及腰
部,女性则要被埋及颈部。如今的宗教法庭规定行刑用的石块要足够
小,一方面要避免受刑人过早地一命呜呼,另一方面也要足以造成确实
的肢体损伤。一次石刑短则10分钟,长则20分钟。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0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83%的巴基斯坦人认为通奸
犯应用该刑处死。据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称,就在2008
年,有1000多人目睹了索马里一名年仅13岁的女孩被石刑处死的过
程。[28]
斩首作为最迅速也最人道的处决方式,适用于那些故意杀人和集体
叛教的罪犯。在21世纪的人看来,斩首等古老的行刑方式似乎已被抛诸脑后。然而,在过去10年中,伊斯兰极端分子采用这种方式惩罚某些西
方人。有人认为,这种方式起源于古代中东地区,曾一度被所有主要宗
教采用。公元627年,先知穆罕默德下令用斩首的方式处死600名麦地那
附近的犹太部落成员,理由是他认为他们犯了通敌叛国罪。巧合的是,他最宠爱的孙子侯赛因·宾·阿里(Hussein bin Ali)于680年在卡尔巴拉
(Karbala)被斩首,且首级被盛在银盘中,经由大马士革送往开罗。斩
首在今日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仍是官方惩罚手段。在沙特阿拉伯,仅
2003年就有52名男子和1名女性被斩首,他们所犯的罪行从杀人、抢劫
到同性恋、贩毒不一而足。如今,罪犯在被带往公共广场之前往往先会
被注射镇静剂,蒙上眼罩,戴上脚镣,双手铐在背后,然后被斩首。虽
然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反复呼吁,但沙特人严守伊斯兰律法,对一系列
罪行实施死刑。实际上,大部分沙特公民被处决的可能性很小,而大多
数贫穷的外来劳工往往更有可能成为刀下鬼。但1977年,该国开国国王
的曾孙女与其情人却双双被处死,她本人遭枪决,其情人则被斩
首。[29]
大多数神职人员之所以指责恐怖分子将斩首作为惩罚手段,不
是因为这种举动是非伊斯兰式的,而是因为它被滥用了。
尽管如此,若是将斩首视为伊斯兰文明所特有的行为就大错特错
了,因为斩首在很多文明中都被用作绞刑、钉十字架或开膛破肚的人道
替代手段。斩首是否真的人道,取决于刽子手的冷静程度。1587年,苏
格兰的玛丽女王被处死时,刽子手可能是喝醉了,砍了三刀才让尸首分
家。英国人在1076年通过了砍头的法律,开始对高等级罪犯适用斩刑。
500年后,对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叛国罪惩处被减刑
为简单斩首,令他免受先被吊个“半死”,然后活生生遭肢解,即“割掉
私处、开膛破肚、灼烧内脏,四肢分挂在四个城门上,首级悬在伦敦桥
上”的酷刑。
在《圣经》时代,火刑是对九种乱伦行为和一种通奸行为的惩罚。
火刑,或许是因为象征着通过刑罚让罪人得到净化,因而更多地被用于
道德犯罪。有了针对部族相残的禁令后,对体罚的设计少了些血腥,但残酷程度丝毫不减。到了后《圣经》时代,那些因乱伦和通奸被定罪的
人会被判处缢毙。行刑时,两名见证人各执绳子的一端,绳子用光滑材
料包裹,以免划伤受刑者的脖子。当死刑犯张嘴奋力呼吸时,熔化的铅
水就会被灌进他的喉咙,烧灼其内脏。
古代以色列人使用的更痛苦的体罚之一是棒刑,该刑罚适用于168
种罪行,包括7种乱伦行为、8种违背饮食教规行为、3种祭司违反婚姻
法的行为、与私生子或基甸人的后代通婚、与经期女性发生性行为等。
在后《圣经》时代,鞭刑和棒刑的上限是40次;渐渐地,人们意识到应
该根据罪犯的身体条件适度行刑,也就是说,量刑以法庭估计的罪犯的
承受度为限。以40次为上限的做法体现了更人道的精神。埃及
埃及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大约同时兴起,却有着天壤之别,这在很大
程度上要归功于邻近的广阔沙漠为其阻挡了潜在的入侵者。埃及几千年
的历史比苏美尔王朝延续得更久,主要是因为后者位于开阔的平原上,便利的地理条件成了持续不断的战争的温床。相反,埃及的地理位置相
对孤立,在这里居住的种族也更单一,因此,与古代近东地区的众多文
明自相残杀不同,埃及人学会了在尼罗河沿岸共存,共同抵御每年一次
的洪水,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埃及文明能持续27个世纪。[30]
我们关于埃及早期罪与罚的认知,用一名埃及学家的话说,乃是来
自“法庭文件、市民契约、私人著作、行为举止、虚构故事和一些王室
法令的随机组合”。[31]
从这些资料里可以看出,埃及的罪行包罗万象,从末经许可强借驴子,到盗窃、暴力抢劫、诈骗、逃税、谋杀和罪大恶
极的弑君罪等听上去更现代的罪行,不胜枚举。按照现代西方的标准,埃及人对有罪者的惩罚既迅速又严酷。那些被定罪的人,轻则被判苦
役、鞭笞或各种肉刑;重则要受桩刑,被“置于木桩顶端”缓慢、痛苦地
死去。最高法律实施者代表着国家权力,因此古埃及法老是法律的最终
制定者,有权引入新的法律和惩罚手段。
根据一些保存最完好的关于第十九王朝塞提一世(Nineteenth
Dynasty of Seti I)时期的资料,对偷盗神明供奉者的惩罚包括“杖两
百,割五刀”。但痛苦的杖刑、割刑、断肢刑和死刑,既是为了让受刑
者蒙受痛苦与屈辱,也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重申其作为警告他人的权
力”。[32]
自第十八王朝起,体罚和(或)经济惩罚成为常态,死刑也在
国家颁布的一系列惩罚手段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彼时,埃及几乎
不使用货币,这意味着赔偿主要限于“肉刑和劳役”。正是在这一时期,“欠税者马利成了(或许是)第一个因被判鞭刑而名留史册的埃及
人”,他因“不实诉讼”挨了一百鞭。[33]
到第十八王朝末期(公元前13世纪),对罪犯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观
点已成为规范。严刑峻法被用于惩治官员腐败。如果一个人因阻止尼罗
河上的自由通行而被判有罪,他将被割掉鼻子,流放到西奈沙漠的一个
社区。各种新残害被用来标记罪犯(从而确定他们的罪行)。割耳和割
鼻最为常见,适用于苦行犯,因为面部的损毁并不会妨碍劳动。有学者
认为,当时的社会中可能不乏畸形人,他们的身体要么毁于疾病或糟糕
的医疗技术,要么在可怕的意外事故中受伤,因此面部损毁和其他残害
带给公众的惊惧可能并没有如今那么强烈。割鼻和割耳虽然痛苦,却很
少导致死亡或并发症。由于这两个器官主要由软骨构成,基本不参与血
液循环,因此出血的风险极低。受刑者或许会出现呼吸或听力问题,但
这对身体的损害远小于削手和断肢。[34]
死刑主要适用于背叛国家(国王以及他所代表的神圣秩序)的罪
行,相比其他古代社会,埃及的死刑判决似乎相对较少。人类历史上现
存最早的书面死刑判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6世纪的埃及,当时一名罪犯
因施魔法被判死刑,且被要求自裁。处决往往是公开执行,虽然场面不
如后来古罗马斗兽场中的那般精彩,却是国家对潜在违法者的警告。当
涉及叛国、叛乱和通奸罪时,这种意味尤为明显,罪犯有时会被处以火
刑。在其他情况下,平民处决的首选方式是被钉在木桩上,而对杀人犯
则适用斩首。[35]
与大部分古人一样,埃及人将弑亲视作最严重的罪
行,并给予更严酷的惩罚。弑亲者会赤身裸体滚过荆棘,然后葬身火
海;若母亲杀了孩子,则会被迫将孩子的尸体绕在脖子上,直到其腐
烂。
官方使用的三种逼供方法包括笞打脊背和四肢、威胁放逐到努比亚
(Nubia,苏丹),或斩断部分肢体。最常见的体罚形式似乎是鞭笞,残害则适用于更严重的罪行。杀父母者要被碾过荆棘然后活活烧死。犯通奸罪的男性会被处以1000下鞭刑,女性会被割掉鼻子。强奸犯会被阉
割,叛徒则会被割掉舌头。
从理论上说,同样的法律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即使是最富有的贵
族也不能逍遥法外。任何等级的人如果犯叛国罪这样的罪行都会被严
惩。埃及的文献中充斥着抢劫、偷窃、入室盗窃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的记
录,包括团伙盗墓并抢劫,其年代可以追溯到拉美西斯九世(Ramses
IX)统治时期。
埃及人相信每个人都有肉体和灵魂,并将肉体的死亡视作生命的中
断,而非终止。此外,他们相信随着死亡的到来,死者将面对奥西里斯
(Osiris)和地狱四十二判官的审判。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死后不得安
葬。正因如此,处以火刑会对亡者无尽的阴间生活带来极大伤害,因为
没了躯体,亡灵就无法通过审判。一个人的来世或受折磨或交好运,影
响来世的一系列律法在埃及的《亡灵书》(Book of the Dead)中均有记
载。古代中国
3000多年前,《易经》以非常含蓄的方式提到了一种名叫“何校”的
惩罚:“何校灭耳,凶。”校即枷,是一种笨重的木质项圈,约3~4英尺
见方,中间开有一孔供头伸出。枷被固定在佩戴者的脖子上,其宽度使
得佩戴者的手无法触及面部。视情况而定,罪犯会被判戴枷1至2个月不
等。通常而言,这种惩罚含有羞辱的意味,戴枷者要被迫坐在其实施犯
罪行为的地方。到了夜晚,他会被一个官员带回牢房,如果运气好,他
可能会被允许摘下木枷,直到第二天。此外,倘若没有人为他提供食
物,他还不得不靠乞讨为生。
帝制时期的中国刑罚制度源远流长。古中国的刑罚与西方和近东地
区建立的制度和传统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或
天然、或人为的与世隔绝状态。孤立保障了中国司法体系得以独立发
展,不受或多或少源自美索不达米亚法律的中东法典和欧洲法典的影
响。
到公元前22世纪,中国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在很多情况下,人
类早期社会为惩治恶行而发展出的刑罚手段大同小异;而在中国,即便
是早期,惩罚手段的划分也相当清晰,从罚款、黥到笞、劓、刖、宫等
肉刑不一而足。此外,它有一个突出特点:衣着服饰也是惩罚的一部
分。受黥刑的罪犯只能戴头巾,不能戴帽子,因为后者会遮挡其面部。
那些被判刖刑的罪犯可以穿麻衣,但不能穿丝绸服饰或草鞋。受宫刑的
人不得穿长袍,只能穿及膝短袍,(截短的袍子)表示他遭受了阉割之
刑。类似地,被判斩首的人只能穿无领短衣。但这些惩罚手段显然只适
用于那些罪大恶极的行为,因为律法中还规定了各种宽大条款。与后来
的不少社会一样,只要有可能,流放往往成为代替刑罚的手段。杖笞是宋朝(960—1279年)常见的刑罚。根据法律,行刑用竹
杖,上限为40下。行刑规范要求罪犯趴在地上,解开臀部周围的衣物,以臀部接受杖打。如果是女犯,则可以跪在地上,只脱去外套,以背部
或腿部受刑。刑罚的严酷程度取决于笞打的力度而非次数,贿赂行刑者
以求手下留情的现象自然免不了。还有一种肉刑是用1尺长的皮条(2~3
英寸宽)抽打脸部。行刑时,罪犯跪在地上,行刑官一只手抓住罪犯的
头发,一只手用皮条抽打。抽打次数被限定在20到30下,但这并不能避
免罪犯的嘴唇时有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情形。[36]
虽然超出常人想象力
的非法酷刑的确存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刑罚限于流放、监禁和斩
首。古希腊
古希腊是数百个独立和半独立城邦的集合体,而非一个统一的国
家。在这些城邦中,雅典声名远播,几乎成了希腊在古代的代名词。形
成于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法典在很多方面皆异于早前的近东法典和摩西
律法。与万能的汉穆拉比王颁布的法律和由摩西律法所代表的上帝之法
不同,雅典律法乃是基于民众的意见。大体而言,希腊人吸收借鉴了美
索不达米亚律法和东方法律的思想,并塑之以西方特色。不过,与古代
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并未直接接触东方文化。这两种文明之间有着天
壤之别。在美索不达米亚,国王是绝对的统治者;而希腊人,至少是雅
典人,却对公民权利有着基本的尊重。但无论如何,希腊法律毫无疑问
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希伯来律法的间接影响。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古代雅典人非常害怕成为暴力的受害者,或在
大街上或公共场所被抢劫财物。[37]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普罗塔哥
拉和其他雅典人很早就提出了贫穷与由贫富差异造成的罪犯之间的因果
联系。尽管如此,贫穷并未因此成为偷盗、抢劫等罪行免遭惩罚的理
由。被抓的抢劫犯与入室窃贼若不能在审讯中提供任何辩护,将被依法
处决。处决常常含有某种公开羞辱的意味,罪犯会被钉在木板上慢慢等
死,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勒死。在罪犯被处以罚款的情况下,也可以同
时附加某些羞辱刑,比如束缚在枷具上五日等。
在荷马时代(Homeric Age,前8世纪),古希腊出现了刑法制度的
第一次重大飞跃,正义的齿轮开始绕着受害者与罪犯之间的非正规程序
旋转。在通奸、诱奸和强奸案中,应由被戴绿帽子的丈夫或其最亲密的
亲属(当受害人是自由女性时)来主张正义;若受害人是奴隶,则由其
主人提出诉讼。偷牛、抢劫和海盗等罪行不仅常见,而且威胁到整个社
会,因此应由社群提出集体诉讼。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凶杀案,凶手会被放逐。如果行凶者和被害人没有亲属关系,则行凶者通常会尝试逃亡
或支付赔偿,以免死于受害者家人的怒火之下。
古希腊的第一部成文法当归于政治家德拉古。公元前7世纪,他受
命编写一部新的法典,以遏制氏族仇恨、控制民众动乱。据说,他对几
乎所有违法行为都残酷无情地施用死刑,“严酷的”(draconian)一词便
由此而来。对德拉古的法典,我们基本上只能通过后世希腊历史学家的
著作来了解一二。据普鲁塔克记载:“就连那些偷沙拉或水果的人也会
受到与亵渎神明或谋杀犯相同的惩罚……德拉古的律法不是用墨水,而
是用鲜血写成的。”[38]
不过,我们对希腊历史早期的罪与罚的实际了解
仅限于那些涉及凶杀的案件。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司法革新是建立了专门
审判杀人案、纵火案和其他严重罪行的雅典最高法庭(Court of
Areopagus)。我们能够确知的是,受害人在临死前拥有宽恕凶手的权
力,可使凶手免于惩罚。稍晚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证实了这
一点,他写道:“如果受害者本人在死前为凶手开脱了罪责,则其他家
庭成员不得继续控告他,除非凶手已被定罪;驱逐、流放和死亡由法律
决定,罪犯一旦被赦免,就不再受其他任何控诉。”[39]
为了避免无止境的仇杀,德拉古法典给了凶手三个选择。他们可以
认罪并被立即放逐;可以服从审判,在判决确定前遵守规定并依旧享有
自由,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得出现在祭祀和公共场所;他们还可以不选前
两条路,不过倘若如此,罪犯有可能因出现在公共场所或圣地而被雅典
人当场杀死或逮捕(这是市民拘捕的雏形)。在德拉古的法典中,我们
可以看出对正当杀人与不正当杀人的区分,二者适用不同的处罚。只有
在预谋杀人或主动杀人案中,城邦才有权做出死刑判决。同时,法律允
许受害者家属接受赔偿,以代替城邦处罚。
与其他类型的犯罪不同,杀人案的诉讼期不受时间限制,受害者家
属对侵害者的合法报复也不受时间限制。如果受害者家属不采取行动,就会让家庭蒙羞。此外,雅典人担心有罪之人会因未被及时发现而逃脱审判。这一点对现代司法影响深远,在美国,谋杀罪仍是少数没有诉讼
时效的罪行之一。由于资料匮乏,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罪与罚的认知仅限
于杀人罪。我们知道,非故意杀人的罪犯会被处以刑期不定的流放,只
有当受害者亲属同意时,流放方能结束。当时的一段文字记录了一名被
判终身流放者的话,他哀叹道:“若被判死刑,我所做的恶将会令子孙
蒙羞;若被流放,我将无家可归,在异乡乞讨终老。”[40]
被流放的罪犯
在流放期间会受到保护,免遭暴力或威胁,如果他受到伤害,行凶者将
被惩罚。然而,一旦他提前从流放地返回,他所受的保护也将不复存
在,很容易成为复仇者的目标。
故意杀人、行凶、纵火、投毒案会在雅典最高法庭审理(非故意杀
人行为不受惩罚)。随着时间的推移,处决工具从沉重的木头变成了
剑。用于行刑的木头究竟是何模样,目前尚存争论,但有可能类似棍
棒。考古学证据显示,还有一种处决方式规定,要把罪犯的脖子、手腕
和脚踝分别用五根铁箍固定在一块直立的木板上,然后或者任由他忍饥
挨饿慢慢死去,或者按照有些人的说法,收紧绕在罪犯脖子上的铁箍将
其勒死。
希腊人提到“穿石衣”的做法,我们可以推断,石刑在古希腊是一种
正式的处决手段。早期希腊的刑罚制度在多数情况下允许适用赔偿方
式,对杀人犯和叛徒则往往适用投石处死或毒芹处死。英雄时代的希腊
人也采用坠落处死的方式,即将罪犯扔下绝壁。这种刑罚往往也包括把
罪犯猛地从高石台上扔下或推进深坑,由于坑里布满专门用来刺穿身体
的尖刺和钩子,因此可以确保其死亡。到公元前5世纪,毒芹取代了深
坑。与此同时,绞刑、钉十字架和用棍棒殴打致死的方式也投入使用。
与斩首、断头台、现代毒气室、电椅和注射死刑一样,毒芹的使用标志
着死刑人道化的早期尝试。在众多使用这种从种子和茎叶中提取的黏稠
毒剂的案例中,最著名的当属对70岁的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处决。公元前
399年,他因败坏雅典青年、拒绝承认城邦神灵的罪名被判死刑。死于
毒芹之下当然不舒服,死亡常常伴随着痉挛和抽搐,但这种方式仍被视作不流血的文明手段。
偷窃某些蔬菜和水果、亵渎圣物、游手好闲和杀人都是死罪。事实
上,德拉古法典或许并不比传统习惯法更残酷,但因其未对法律体系做
出任何彻底变革,因而招致雅典民众的不满,留下了恶名。德拉古法典
代表了从前文字时代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变。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
人们遵守某种固定不变的法律程序,并给出了各种罪行的预定惩罚。为
了公示于众,法典中关于宗教的条款被刻在木头柱子上,其他条款则被
刻于铜柱之上。
到了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对杀人罪的态度变得令人
费解。与早期其他社会的做法一样,受害者家庭有责任寻求惩罚或复
仇。然而,这绝非单纯的“以眼还眼”。除了复仇之外,赎罪也必不可
少,也就是说要让城邦免受杀人罪行的污染。人们认为,凶手的手是肮
脏的——被罪行玷污了——且会污染所有和他接触的人以及发生罪行的
整个城邦。为了净化城邦,要由受害者家属决定,或者对凶手实施复
仇,或者达成某种和解,让受害者家庭能最终宽恕凶手。[41]
雅典人是名副其实的爱国者,任何不忠诚或背叛的行为都会被视作
最严重的罪过,将被城邦判处死刑并没收财产。但对很多罪犯而言,最
糟糕的莫过于死后不能埋在雅典。据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录,特米斯托
克利因叛国罪被处决后,他的朋友将其尸骨偷偷带回雅典埋葬,这便是
极好的例证。抢劫神庙、施魔法或破坏神像的行为,其惩罚几乎可以与
叛国罪等同。与早前(及后来)的文明相比,当涉及道德犯罪时,希腊
人的态度明显温和得多。在大多数时候,而罪犯受到的最严厉的处罚也
不过是被拔掉体毛或肛门里被插进一根小萝卜。[42]
但若涉及通奸且被
当场抓获,愤怒的丈夫有权杀死通奸者。这条规定出自德拉古法
典:“如果一名男性杀死了与他的妻子通奸的人……他不会因为该行为
被判杀人罪而遭流放。”当然,他也可以接受金钱补偿,放弃个人报
复。造假币的古老手艺
古代和现代的犯罪形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大多数古老的罪行以这样
或那样的方式摇身一变进入了现代法规。以杀人、抢劫和盗窃为例,这
三种行为很早就被认定为罪行或恶行,尽管具体定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有
所变化。这一点在经济案件中犹然。随着生活日益繁复,且涉及了各种
法律条文,人们有必要通过某种形式的账目来记录一些基本事项,诸如
仓库里有什么货物、市民是否向公共基金缴了应缴的款项。例如,在美
索不达米亚,每个人都要向神明提供供奉。但出于人类的本性,很多人
会设法逃避(就像今天的人逃税那样),声称他们已经“付过了”或捐献
过了。用楔形文字或埃及象形文字记录的账目不仅使文明社会得以采用
更高级的统治形式,也确保了特定责任得到履行。
早在公元前3000年,继书写和有组织耕作之后,货币作为另一种文
明迹象也出现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尽管如此,早期的货币乃是金
银,而非铸币,因此其价值取决于交易金属的重量。别忘了,人类的本
性中有着对犯罪行为不同寻常的偏好。很多证据表明,人们自古便试图
伪造金属货币,后来则发展成伪造皇家铸造的硬币。受德拉古的影响,公元前7世纪的梭伦成了法治的热情支持者,他坚持认为,只有严惩偷
窃或挪用公款等罪行,法治才能向前推进。
相比之下,《圣经》不太重视涉及财物的犯罪,不像古代世界其他
地方的法典那样对该类犯罪适用体罚或死刑,而是判处支付罚金和赔
偿。
到了古罗马帝国时期,伪造者的技艺已相当精湛,掌握了用来浇铸
金属的陶土磨具的制作工艺。历史资料显示,伪造者会被处以最严酷的
刑罚。君士坦丁大帝曾将这些人活活烧死。从硬币上切削、熔化稀有金属的人会被“切削或割掉”耳朵。其余相关罪犯会被剥夺公民权。随着帝
国的壮大,伪造者若是不被阉割或扔进狮笼,至少也会被割掉鼻子。尽
管如此,当帝国日薄西山之际,伪造之风却在古罗马贵族间悄然兴起。
严惩伪造者的做法也延伸到其他社会。随着公元8世纪伊斯兰教的
不断扩张,伪造者会被处以剁手之刑。在7世纪的中国,对伪造者的惩
罚是黥面,之后发展到死刑。到了14世纪,中国甚至在钱票上印着“伪
造者处死”的警告。[43]奴役和监禁
奴隶制度贯穿人类的整个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奴隶的社
会不在少数,包括希腊人、朝鲜人、印度人、美洲原住民、古罗马人、维京人、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建立的社会。大多数观点认
为,奴隶制“在所有古代文明社会中都被视作自然和合理的社会制
度”。[44]
奴隶的生命都比较短暂,埃及人用奴隶为皇室成员陪葬。事实
上,在不少社会中,人们购买奴隶的主要目的正是作为牺牲。不过,在
很多情况下,奴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强制劳动,也是一种惩罚制度。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提到,公元前11世纪,埃塞俄比亚国王萨巴
科斯(Sabacos)——此人后来也成了埃及的统治者——用“想必也伴随
着监禁”的强制劳动取代了死刑。与19世纪基于人种的奴隶制度不同,在当时,人种并不能决定某人是否会受奴役。在古代刑罚实践中,人们
更常用罚款或放逐作为惩罚手段,除非需要大量劳动力去完成某个超出
早期社会能力的工程。在足够先进的技术出现之前,奴役劳工是获取大
量劳动力仅有的几种方式之一。因此,只有当需要调动劳动力开采稀有
金属,修建金字塔、道路和纪念碑时,强制劳动才会成为社会的惩罚手
段。[45]
从我们现有的少量证据中可以看出,蓄奴出现后,将奴役作为惩罚
手段便失去了明显的意义。不过,这个变化在古代近东地区和古希腊并
不突出。在埃及,因罪沦为奴隶的主要原因是欠了国家债务。在古代朝
鲜,因叛国、抢劫和屠杀珍贵家畜而被定罪的人,其家属将沦为奴隶。
在中国汉朝以前,死刑犯的家属会成为奴隶。自此,因罪成奴不仅是主
要的,也是唯一被认可的奴隶来源。因此,中国的奴隶制与惩罚制度相
伴相行。所有犯了罪并被判奴役的人通常都会被刺上某种刺青或毁容,以区别于自由民。这种罪犯标记乃是人口买卖的最重要的基础。此外,与近东和西方不同,中国的刑事制度强调家族纽带和责任,一人犯罪,其家庭成员和旁系亲属往往都会受牵连。[46]
在不使用奴役作为惩罚手段的早期社会里,为了强迫债务人还债或
控制那些等待审判和惩罚的罪犯,必然要使用某种形式的监禁措施。古
代监狱与现代监狱的区别在于,早期的监狱不是专门建造的。大部分关
于古代刑罚的历史记录都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与现代刑事体系的其他诸
多方面一样,监狱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当然,究竟早到何时,目前并没
有确凿的证据,但坟墓、处决室和在战争中用于关押奴隶的地方已存在
了数千年。关于这方面的最早期信息的确相当匮乏,但在埃及象形文字
记录、希腊神话和《创世记》中绝非一笔带过。将某人关押起来然后扔
掉钥匙的做法自古有之。
纵观历史,早期社会追求的是迅速、确定的惩罚,无论断肢、罚
款、流放或死刑皆是如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监禁亦属于这一类惩
罚。现有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古代埃及,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建筑奇
阿普斯(Cheops,希腊人对胡夫的称呼)大金字塔(约前2650年建成)
内有个地下深坑,据说是“迷失者的牢房”。与此类似,几百年后,埃及
人把建于第六王朝泰蒂(Teti,约前2345—前2333年)时期的萨卡拉
(Saqqara)金字塔称作“金字监牢”。坐落于它东边的另一座金字塔,其
阿拉伯语名称的意思是“卓瑟的监狱”。在国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
和其他地方保存着大量关于在这些古迹中实施监禁的图画。1799年被发
现的罗塞达碑上甚至多次提到了监狱。最古老的埃及墓地可以追溯到
5000多年前(位于尼罗河对面的孟斐斯遗址),而监狱的符号可追溯到
古埃及象形文字中“房子”和“黑暗”的结合体。当然,除此之外,我们几
乎一无所知。还有大量猜测认为,金字塔是由监狱罪犯所建。[47]
《创
世记》(39:20~40:5)中提到了监禁,古巴比伦人曾使用bit kili关押欠
债者和轻罪罪犯(前3000—前400年),亚述帝国则使用bit asiri(前746
年—前539年)。《旧约》记载了埃及人、亚述人和古代以色列人对监
禁手段的使用。在尼布甲尼撒时代,耶路撒冷至少有三座监狱,分别是:Beth ha—keli,或称拘禁室;Beth haasourim,字面意思是“锁链
室”;以及Bor——地下室。
监狱在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资料中也有记载。《尚书》(或称
《书》)提及夏王芬曾建监狱。[48]
雅典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过不
同的刑罚,其中包括罚款、没收财物、公开羞辱和拆毁罪犯的家
园。[49]
雅典的自由民很少被关入监狱,除非是涉及叛国罪或需要用强
制手段迫使债务人偿还城邦债务的情况。那些面临酷刑或死刑处罚的罪
犯会被囚禁,让他们在受酷刑之前先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雅典,甚
至有一座名为“锁链之地”的建筑,虽然或许修建的初衷并非是要作为监
狱。监禁和奴役常常出现在柏拉图(约前300年)的笔下,在他看来,二者都是好政府的必备要素。苏格拉底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接受入狱惩
罚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在《法律篇》中,柏拉图提出,城邦应该有三
座监狱:一座位于市场附近的公共监狱,用于关押普通罪犯;一座位于
夜间议事会(Nocturnal Council)附近的“改造中心”;另一座要在荒郊
野外,并配以彰显惩罚意味的名字。柏拉图建议应根据罪行的严重程
度、罪犯的“本性”和具体的犯罪情形确定监禁期,最长可判终身监禁。
不过,他虽阐述了关于监禁体系的理论,却没有证据表明他的这些观点
在当时得到实际应用。[50]
1860年,小说家纳萨尼尔·霍桑参观了位于古罗马的马梅定监狱
(Mamertine Prison)。[51]
公元68年,正是在这里,圣徒保罗被尼禄处
死。这座位于市场里的宏大建筑是专为等待处决的罪犯准备的监牢,起
初叫carcer(监牢),从中世纪起被称为马梅定监狱,“监
禁”(incarcerate)一词由此而来。私人监狱(carcer privatus)在古希腊
和古罗马均偶有使用,主要关押欠债者和等待审判或处决的人。古罗马
的第一部成文法(参见第二章)《十二表法》(Twelve Tables)提到了
被称为ergastalum的强制拘禁所。不过,各种监牢中最令人胆寒的当属
dungeon。该词源自拉丁文dominium,指的是建在绝壁上的城堡或要塞,后来在法语中演化成donjon,之后又变成了那个我们更熟悉的英语
词。随着时间的推移,dungeon成了地牢和黑牢的同义词。小结
在复杂的法律、审判和监狱体系建立之前,早期社会依靠习俗、巫
术和宗教来维护社会秩序,而彼时的习惯法往往比现代成文法更死板。
在国家诞生之前的社会里,律法常常或源出神明或由部落首领确定,通
过判决或立法程序制定法律的方式则要晚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
段,法律都被视作神明直接命令的衍生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完
整法典描述了太阳神(也是正义之神)沙玛什(Shamash)登上宝座并
将法令交给虔诚的苏美尔国王汉穆拉比的故事。[52]
与此类似,几个世
纪之后,当摩西登上西奈山时,耶和华亲手将《十诫》刻在两块石板
上。虽然《十诫》中的某些条文可以从《汉穆拉比法典》中找到踪迹,但在希伯来人的故事之前,《十诫》本身并不存在。有学者认为,最早
的与《十诫》类似的叙述可见于埃及人的《亡灵书》第125章,书中提
及进入公正之地的死亡宣言:“我从未轻慢神明。我从未杀人。我从未
教唆他人行凶。我从未通奸或行不洁之事。我从未偷盗。我从未说
谎。”无独有偶,据说克里特之王米诺斯(Minos)每9年就要登上奥林
匹斯山接受宙斯的法律忠告。
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程序影响了很多同时代的国家,包括埃及、波
斯和印度,但其在上述地区的影响力并不如在西方那么深远,也未
能“扎下根”。[53]
《汉穆拉比法典》继续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的惩罚程
序,古希腊和古罗马在与近东接触之后均受到了它的影响。伊斯兰国家
在征服了如今的伊拉克地区之后也有了法典。早期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
人通过对民众认可的特定法律原则的确认完成了立法。而在相对更孤立
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中国文明和埃及文明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关于罪与罚
的理念。
最早的法典几乎完全由惩罚条款构成,着眼于惩罚那些最危险的罪行,比如杀人和人身伤害。由于社会发展受制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彼时
的惩罚手段不似后来那般多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谓刑罚只是简单地
以命抵命或其他同态惩罚(以相同的手法和相同的程度进行处罚)。一
些世间最常见的罪行及其惩罚可以追溯到古代,其中包括石刑、绞刑、斩首和钉十字架。由波斯人或古代腓尼基人发明的十字架被亚述、古埃
及、古希腊、印度、迦太基、凯尔特和古罗马等文明古国广泛采用,直
到315年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后才淡出历史。[54]
不过,日本直到19世纪
仍在使用十字架刑。钉十字架传统上是一种政治或军事惩罚手段,迦太
基人和波斯人用它来处决军事指挥官和高级官员。古罗马人则喜欢用十
字架对付下等人、奴隶和暴力犯。严刑峻法以约束民众的理念强化了依
身份量刑的观念,并影响着随后的几个世纪,给贫穷无助的劳苦大众带
去了最深切的苦痛和折磨。
[1]Jean Guiliane and Jean Zammit,Origins of War:Violence in Prehistory(Oxford,2005),p.231.同
时参见Ian Armit,‘Violence and Society in the Deep Human Past,’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LI(2011),pp.499~517。
[2]Ronald Hutton,Pagan Britain(New Haven,CT,2014).
[3]Karin Sanders,Bodies in the Bog and the Archeological Imagination(Chicago,IL,2009),.4.
[4]Karin Sanders,Bodies in the Bog and the Archeological Imagination(Chicago,IL,2009),.4.
[5]R.S.Rattray,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London,1911),pp.232~233.
[6]R.S.Rattray,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London,1911),p.292。
[7]R.S.Rattray,Ashanti Law and Constitution(London,1911),pp.372~375。
[8]为了避免在行绞刑时造成肢体残缺或出血,通常会使用皮绳或徒手操作。当使用棒刑
时,通常会用象牙或某种杵来打死高等级的受刑者。参见拉特雷的Ashanti Law,p.375.
[9]为了避免在行绞刑时造成肢体残缺或出血,通常会使用皮绳或徒手操作。当使用棒刑
时,通常会用象牙或某种杵来打死高等级的受刑者。参见拉特雷的Ashanti Law,p.376。
[10]Jacques Barzun,From Dawn to Decadence:500Years of Western Cultural Life,1500to the
Present(New York,2001),p.762.
[11]Robert H.Lowie,Primitive Society(New York,1920),p.401.
[12]Robert H.Lowie,Primitive Society(New York,1920),p.416。
[13]Karin Bullard,“‘Blood Money’could Free American”,Houston Chronicle,5March2011,p.A14.[14]Lowie,Primitive Society,pp.413~414.
[15]Jo Tuckman,‘Vengeance Allowed to Flourish’,Houston Chronicle,30June2002,p.24A.
[16]Reed Lindsay,‘Bolivia’s Aymara Taking Justice into Own Hands’,Houston
Chronicle,26September2004,p.A30.
[17]1英尺≈0.3米。——编者注
[18]大多数已被后来的伊拉姆征服者带到苏萨,并于1901年被发现,如今保存在巴黎卢浮
宫博物馆。
[19]Marc Van De Mierop,King Hammurabi of Babylon:A Biography(Malden,MA,2005),p.99.
[20]虽然我们知道“玉米”是在美洲被发现的,但在前殖民时代,这个词也被用来指代“谷
物”或当地生长的其他各种主要农作物。
[21]米那:古希腊、古埃及等之重量及货币单位。——编者注
[22]Frances F.Berdan,‘Crime and Control in Aztec Society’,收录于Organised Crimein
Antiquity,ed.Keith Hopwood(Swansea,2009),pp.255~270.
[23]Alan Milner,The Nigerian Penal System(London,1972).
[24]Lowie,Primitive Law,pp.402~403.
[25]‘Divorce’,收录于Encyclopaedia Judaica,2nd edn,vol.v,ed.Fred Skolnick and Michael
Berenbaum(Farmington Hills,MI,2007),p.710;同时参见Ruth3:9。
[26]Israel Drapkin,Crime and Punishment in the Ancient World(Lexington,MA,1989),p.32.
[27]Victor H.Matthews and Don C.Benjamin,Social World of Ancient Israel,1250—
587BCE(Peabody,MA,1993),pp.11~12.
[28]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2009,‘Pakistani Public Opinion:Growing Concerns about
Extremism,Continuing Discontent in the United States’,at http:pewglobal.org.
[29]‘Saudis Defensive as Swords Swing,Heads Roll’,Houston Chronicle,25April2000.
[30]Drapkin,Crime and Punishment,p.37.
[31]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
[32]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p.65。
[33]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p.72。
[34]Joyce Tydlesley,Judgement of the Pharaoh:Crime and Punishment in Ancient
Egypt(London,2002),p.72.[35]Pierre Montet,Everyday Life in Egypt in the Days of Ramses the Great(New
York,1958),p.269.该书作者认为,受刑者只是被绑在柱子上等死,而非被刺死。
[36]The Strange Cases of Magistrate Pao:Chinese Tales of Crime and Detection,trans.Leon
Comber(Rutland,VT,1964).
[37]Nick Fisher,“‘Workshops of Villains’:Was there Much Organised Crime in Classical
Athens?”,收录于Organised Crime in Antiquity,ed.Hopwood,pp.53~96。
[38]Plutarch’s Lives(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vol.I,trans.Arthur Hugh
Clough(New York,1992),p.117.
[39]Demosthenes,转引自Douglas M.MacDowell,Athenian Homicide Law in the Age of the
Orators(Manchester,1999),p.8。
[40]Demosthenes,转引自Douglas M.MacDowell,Athenian Homicide Law in the Age of the
Orators(Manchester,1999),p.113。
[41]Demosthenes,转引自Douglas M.MacDowell,Athenian Homicide Law in the Age of the
Orators(Manchester,1999),p.113.
[42]Herbert A.Johnson,Nancy Travis Wolfe and Mark Jones,History of Criminal Justice,3rd
edn(Cincinnati,OH,2003).
[43]John K.Cooley,Currency Wars:How Forged Money is the New 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New York,2008),pp.56~62;本部分的标题取自库利书中的同名章节,p.55。
[44]J.Thorsten Sellin,Slavery and the Penal System(New York,1976),p.1;Orlando
Patterson,Slavery and Social Death: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MA,1982).
[45]M.I.Finley,Ancient Slavery and Modern Ideology(New York,1980),pp.67~68.
[46]Patterson,Slavery and Social Death,p.128.
[47]汉茨维尔市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里占地1.86万平方米的刑事审判中心是在20世纪70年代
由监狱服刑人员建造的。
[48]此处作者引用的典籍应为《竹书纪年》,其中有“夏后芬三十六年作圜土”的记载。夏王
芬,一名“槐”。——编者注
[49]20世纪90年代,以色列国防军在巴勒斯坦人暴动期间使用了类似的策略,推平了巴勒
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和其他与恐怖袭击有关联人员的家园。
[50]Norman Johnston,Forms of Constraint:A History of Prison
Architecture(Urbana,IL,2000),pp.5~6.
[51]此地现在已向公众开放,本书作者最近曾造访过。
[52]苏美尔曾是古巴比伦的一部分,位于古美索不达米亚的南半部,亚述则在北部。
[53]Drapkin,Crime and Punishment,p.31[54]Martin Hengel,Crucifixio(Philadelphia,PA,1978),pp.22~23;Lewis Lyons,The History of
Punishment(London,2003),p.162.第二章 法律传统的兴起
虽然大多数现代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当代四大法律传统上,但在历史
上,至少有16种不同的传统曾繁盛一时。1928年,亨利·威格莫尔
(Henry Wigmore)将这些法律体系分别命名为埃及法系、美索不达米
亚法系、中华法系、印度法系、希伯来法系、希腊法系、罗马法系、海
洋法系、日本法系、伊斯兰法系、凯尔特法系、日耳曼斯拉夫法系、教
会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8年之后,威格莫尔认为,上述法系中
有6个已经完全消失[1]
,5个发生了混合,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法系则基
本保持独立。1936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13年,威格莫尔将中
华法系定义为迄今尚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法律体系。
除了少数实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国家(古巴、中国、越南、朝
鲜)之外,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基于民法传统、普
通法传统或伊斯兰法律传统。当然,采用民法法系和普通法法系的国家
最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殖民势力将这两种法律传统带到了全球。
由于大大英帝国的统治,普通法传统在加勒比、北美、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非洲部分地区、印度等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最年轻,或许也是使用国家最少的主流
法律传统,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于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动荡
年代里诞生的社会主义法系极大地借鉴了民法法典和俄国习惯法。由于
缺乏系统构架,(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特别法官拥有大量自由裁判
权。俄国民法典深受早期俄国、德国、法国和瑞士民法典影响。古巴、朝鲜、越南和中国是如今仅有的采用社会主义法系的国家,但其各自在
罪与罚的实践上迥然不同,无法一概而论。
几个世纪以来,上述法律传统或经由征战或通过殖民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随后在新家园里因地制宜地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见第
八章)。普通法传入新大陆时必须依殖民地环境进行调整,以便既能适
用于荒野化外之地,亦能与众多高度发达的本土社会相互交融。类似
地,当英国人在非洲、印度和亚洲建立殖民地时,他们的法律体系也被
迫同那些已经有自身的罪与罚体系的复杂社会法律体系展开竞争。到20
世纪40年代末,大英帝国日薄西山,但普通法影响下的刑法判例在从津
巴布韦、尼日利亚到大洋洲、北美洲的各前殖民地生根发芽。
鞭刑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实施,比大英帝国的统治期更长久,被用
于行乞、传播色情作品、叛国和暴力抢劫等罪行。1965年新加坡独立
后,其法典中保留了肉刑,甚至在当年将适用肉刑的罪行增加到30种。
最近的一个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旧法律传统在被移植到全新的环境中后是
如何演化的。用白桦木棍笞打是英国殖民司法体系中沿袭近200年的传
统,此类肉刑曾令英国人臭名远扬,以至于被法国人称为“英国之
恶”。[2]
但在1998年3月,英国议会投票废除了笞刑,同样废除该刑罚的
还有其曾经的殖民地新西兰(1990年)、南非(1996年)和苏格兰
(2000年)。然而,笞刑并没有从这个前帝国的偏远角落里消失。1994
年,侨居新加坡的18岁美国人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因受笞刑在
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指责之声多来自西方世界。起初,费伊被控与
53起涉及破坏公共财产的案件有关,最终坐实两项破坏公共财产案、两
起恶作剧和一项藏匿盗窃财产案,并被判有罪。但最令人权观察家愤怒
的是,他被判4个月监禁、2500美元罚款和6下笞刑(申诉后减为4
下)。新加坡受到西方世界围攻,但坚持立场。1994年5月4日,费伊和
其他9名被判同类刑罚的罪犯一起在监狱的笞打室接受了惩罚。他们被
剥去衣服,手脚用带子绑在一张H形的条凳上,肾脏部位被施以保护。
除了行刑手,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一名医务官。一名记者描述道:“行刑
手铆足了劲儿,使出全身力气,挥舞着13毫米厚的藤条。藤条事先已在
水中浸泡了一整夜,以防开裂。藤条抽打在费伊裸露的臀部,每两次之
间大约间隔半分钟。”[3]
整个过程最多用了10分钟。行刑完毕,行刑手和罪犯相互握手,费伊未借助任何帮助独自回到囚室。
虽然新加坡的司法体系根植于英国普通法,但自独立后形成了自己
的法律传统和哲学烙印。不少观察者注意到,英国人喜欢在学校里实施
体罚,这种做法同样被很多前殖民地国家采用。就很多方面而言,新加
坡人已基本抛弃了英国传统,包括在几年前取消了陪审团制度(他们认
为这种制度容易造成错误)。这个城市国家近80%的居民是华人,虽与
中国有不同之处,但其核心价值体系同样强调儒家道德,比如尊重权
威。东西两种世界观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宁可放过罪人也不错杀无辜
的西方观念突显了个体的重要性。相反,亚洲人的观念体现了另一种道
德原则,即宁可错杀无辜以保护大众福祉,不可放过罪人令社会再受危
害。除了考虑到普通法与儒家道德原则的结合,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里
还居住着大量穆斯林,遵从马来穆斯林习惯法的人超过了其总人口的
16%。除了英国普通法,新加坡还存在一个仅为穆斯林设立的单独的宗
教法庭体系。这个例子(以及其他很多例子)说明,法律传统始终在不
断发展,不断与各种传统融合,从而适应人口状况、地缘政治以及全球
化的变化要求。此外,明确划分各法律传统间的界限,并将一个国家的
司法实践归为其中某一种,也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古罗马民法传统
作为现存最古老的法律传统,罗马法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从公
元前6世纪这个位于意大利中部的小共和国成立,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法
成为所有居住在意大利境内的人都需遵守的法律,再到公元3世纪成为
西起大西洋、东至幼发拉底河、北达英格兰和苏格兰、南及撒哈拉沙漠
边界的庞大帝国内所有自由民的律法。随着古罗马帝国扩张到古代世界
的遥远边陲,它也吸收了大量新律法,将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纳入了帝
国。
古罗马人在很多方面都是古希腊人的学生,但说到法律,他们算得
上大师,为现代法律的发展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与其他大多数文明社
会类似,古罗马法律基于数世纪前的不成文习惯法,彼时,立法是上层
贵族的职权。由于法律由上等阶层把持,罪行与处罚对于普通古罗马人
而言始终神秘莫测。到了公元前5世纪,来自下层的反对派强迫立法者
将社会规则编写成法典,以平息人们的不满。于是,《十二表法》成了
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不幸的是,公示于古罗马广场上的原件已在公
元前390年高卢人攻占古罗马时被毁。我们能确知的是,这些法条当时
被刻于十块铜板之上,放在集市供所有人观看和了解。由于遗留的部分
残缺不全,我们只能从后世作品的众多引述中拼凑重现这部法典。相比
严格意义上的实体法,早期罗马法更多涉及程序问题,它是现存最早
的、最重要的法规汇编。
《十二表法》规定了罪行及其相应的惩罚,为我们窥视早期古罗马
社会的文明提供了线索。该司法体系特别关注了在夜色掩护中实施的罪
行。事实上,用于描述偷窃的词furtum正是由furvus(黑暗的)衍生而
来,表明大多数偷窃发生在黑暗笼罩之下。绞刑适用于夜间在他人的庄
稼地里偷偷放牧的罪行;而对焚烧谷仓或谷堆的惩罚是将罪犯活活烧死。变节背叛的高级将领会被用三辆马车车裂。据说,国王宣称这
是“对全人类的警告”。[4]
流放是一种专为社会高等级成员保留的处罚手段;类似的罪行,低
等级成员则要被迫服劳役或被处死。流放分若干种不同形式。比方说,流刑只是将罪犯逐出特定地区,而驱逐出境则意味着不只被长期放逐,还要被剥夺公民身份,没收所有财产。公元1世纪,当涉及杀人罪时,无论是使用武器行凶、做伪证致人死亡还是下毒,贵族都会被处以上述
的流放之刑,而下层民众则没那么幸运,等待他们的是钉十字架或葬身
猛兽之口。[5]
古罗马人精心立法,同样也费心设计酷刑。彼时最著名的一种惩罚
是“袋刑”。这种刑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最初用于惩罚那些杀父
弑母的人。传统的做法是将鲜血淋淋的罪犯与一条狗、一只猴子、一条
蛇、一只公鸡或其他动物缝进皮革袋子里,然后将皮袋扔进河中或大水
池中。接下来的事情可想而知。公元前1世纪后期,庞培律废除袋刑,代之以火刑或被猛兽撕咬。[6]
此外,若古罗马公民按照“犹太礼仪”行割
礼或纵容其奴隶行割礼,将被剥夺所有财产并终生放逐孤岛,施行割礼
手术的医生则要被处死。
早期,对女性的处决是在私下里进行的,因为行刑前首先要剥去她
们的所有衣服。由于规定刽子手不得杀死处女,所以他们要先玷污女
犯。[7]
对其他罪犯的处决则是公开进行,手段包括活活焚烧、野兽撕
咬、丢进塔平岩(Tarpein rock,和希腊人的深坑处决差不多)等等。
公元1世纪和2世纪,角斗是古罗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恢宏的古
罗马斗兽场淋漓尽致地展现着昔日古罗马的辉煌。在那里,奴隶、罪犯
和职业角斗士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着生与死的搏斗,不是互相厮杀,就
是面对从帝国的偏远角落运来的猛兽。然而有一点并不为人所熟知,也
往往被导游刻意回避,即这座斗兽场作为行刑场所的核心角色已有200年之久。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称这种处决是“毫无技巧的屠杀”。但在古
罗马皇帝们看来,这是震慑民众的好机会,可以让他们牢牢记住至上的
古罗马统治者手握生死大权。罪犯们在行刑前夜被马车运来,关在位于
斗兽场地下臭气熏天的小屋里直至次日。罪犯们深知等待自己的将是怎
样的命运,试图自杀的人不在少数。根据塞内加的记载,一名奴隶把头
塞进车轮之间,碾碎了自己的脑袋,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结束了生命。[8]
中午时分,罪犯们被带入斗兽场,分成两组,具有古罗马公民身份
的一组,非公民和奴隶另一组。公民往往先行处决,且得益于他们的公
民身份,他们死得相对痛快些。有些是被刽子手一击致死。也有时,两
名古罗马公民会被一同送进斗兽场,一个人有武器,另一个人没有,有
武器的人要追赶那名赤手空拳的人并将其杀死。一旦完成,幸存者要交
出武器,然后被另一名罪犯追杀。这个过程如此重复下去,直到最后只
剩一名幸存者,而他将被刽子手处决。在此类处决中,施于非公民罪犯
的羞辱也同样落在公民罪犯身上。有时候,身为公民的罪犯会屈辱地与
奴隶一同受折磨。
处决公民罪犯之后,非公民和奴隶就要面对最残酷的死亡,且缓慢
的处决过程往往会占去大部分午休时间。他们被钉十字架,被活活烧
死,被野兽吞噬。这其中许多人是违反了神圣律法,杀人、纵火、亵渎
神殿。基督教作家们记载了大量被野兽撕咬的处决案例。别出心裁的杀
戮无穷无尽。有时,不同的行刑方式会结合使用。比如,奴隶有可能会
先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再被烧死;也有时,他们可能会被绑在某个位置
上,让猛兽恰好能撕咬他们的四肢。神话是古罗马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了打破千篇一律的传统处决方式,古罗马人也会上演各种致命
的神话,由罪犯充当牺牲者的角色。
至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考察钉十字架的处罚方式,这不仅是因为
其象征意义,也是因为围绕这种死刑有很多误解。多数意见认为,发明
钉十字架刑的是腓尼基人,但也有观点认为是波斯人。[9]
这种刑罚后来传入古希腊、亚述、埃及和古罗马。据估计,有数万人死于十字架上。
单单是古罗马,克拉苏皇帝就曾为庆祝胜利在一天之内钉死了6000人。
最初,钉十字架(“极痛苦的”[10]
一词的原型)是一种屈辱的死
法,通常用于处罚奴隶和重犯。在采用十字架刑之前,罪犯只是被简单
地绑在柱子上等死。十字架问世之后,曾有若干种不同的造型,有的是
四臂或三臂,还有的是X形结构。通常,受刑者会被剥去外衣,只留下
缠腰布,而在此之前,他们还要受鞭打,并被迫将十字架的主梁(整个
十字架的重量是一个人无法承受的)扛到行刑地。
近期的研究证实,无论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罪
犯其实都是“缓慢窒息”而亡。事实上,关于如何将罪犯固定在十字架
上,目前仍存在争论。1952年,一名法国物理学家发现,想从手掌处钉
住一名成年人是不可能的。通过使用尸体做试验,他发现,被钉子钉住
的手掌可承受的最大体重是40公斤,只要超过这个重量,手掌就会被撕
裂。通过排除法,剩下的方法要么是用钉子钉住腕骨(这样就能承受整
个身体的重量),要么是用绳子绑在十字架上。无论如何,最终的目标
是要让罪犯的身体悬挂在十字架上,缓慢窒息而死。当身体呈悬挂状态
时,经过一段时间,由于膈和肋间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受刑者只能吸
气(不能呼气),胸腔被越胀越大,最后窒息。这种折磨短则三四个小
时,长则四天。
1971年1月,以色列考古学家宣布他们已鉴定了一具名为约哈南
(Yehohanan,“约翰”的希伯来文写法)的犹太青年的骸骨。该遗骨在
1968年首次出土,很可能是公元1世纪时被钉十字架。这一发现为古代
地中海地区的十字架刑提供了首例铁证。大部分记录表明,十字架刑在
古罗马一直使用到4世纪,直到被君士坦丁大帝废除。然而,早前的证
据至多只是推测,因为人们虽在(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出土的)尸骸的前
臂和脚跟处发现孔洞,却从未能在附近找到钉子。约哈南的骸骨是在一
处埋遗骨的洞穴中被发现的,旁边还有另外几具骸骨。亚兰文字母拼写的名字已模糊难辨。令考古学家们兴奋的是,他的脚踝骨上穿着一根7
英寸长的锈迹斑斑的钉子。研究者分析,这根钉子之所以被留在原地,很可能是因为它被钉在了做十字架的橄榄木的硬节处,因此当锤子砸下
去时,钉子稍稍变形弯曲。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尼库·哈斯(Nicu
Hass)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约哈南之死的过程。按照传统,在经历一系
列死亡前奏之后,约哈南的下肢有可能受到棍子的致命一击,双腿折
断,随后的大出血和休克加速了他的死亡。事后,有人曾试图从十字架
上拔出弄弯的钉子以便移开尸体,但或许是出了什么岔子,固定尸体的
钉子顽固地埋在十字架里纹丝不动。哈斯认为,要将受刑者同十字架分
离,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砍断双足,然后将钉子、木块(用于固定罪犯的
脚)和脚一起从十字架上移开,之后按犹太习俗立刻安葬,以免尸体长
时间暴露在外。一系列事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方才有了这一前所未有
的发现。[11]
若论严刑峻法,古罗马暴君之中当首推卡利古拉,他的名字后来成
了残忍酷刑的代名词。据说他喜欢亲临刑场,边进餐边以此为乐。在一
次宴会上,他命令刽子手砍掉一名奴隶的双手,因为有人指控这个奴隶
偷了沙发上的银带子。之后,他又命人将断手系在那个奴隶的脖子上,在大厅环行示众。卡利古拉追求残酷,开创了惩罚的新境界。他在签署
处决名单前时常咕哝着“我在清理渣滓”。他偏爱共和国时期遗留下的火
刑(活活烧死),把斗兽场当作上演杀戮盛宴的舞台。在一次斗兽表演
期间,他以价格太高为由拒绝从屠夫手中买肉,因为反正有足够的罪犯
可以拿来喂野兽。据说,他站在柱廊间俯视着排成一行的罪犯,命令
道:“杀了那两个秃头之间的所有人!”[12]
有时,卡利古拉会强迫死刑
犯的父母眼睁睁看着儿子被处决。有一次,一名父亲声称自己病得很
重,无法亲自去看儿子被执行死刑,卡利古拉竟派人送去了担架。卡利
古拉的暴虐没有底线。一名士兵在被投入野兽之口前为自己的无辜申
辩,卡利古拉命令将罪犯带回来,似乎是要宽大为怀,谁知他只是将罪
犯的舌头扯下来,然后继续行刑。一名卡利古拉的传记作家称,如果有若干种处决手段可用,卡利古拉定会选择能造成无数小伤口、慢慢折磨
的方式,正如他本人说的“让他感受到死亡的降临”。面对人们的指责,卡利古拉回应说:“让他们尽情地恨我好了,只要他们惧怕我。”[13]
在提比略皇帝治下,所有罪状一律判死刑,且告发者的每一句话都
会被采信。有些被告由于确信只要出庭就会被判有罪,索性直接自杀,逃避注定将至的屈辱和痛苦。
公元4世纪,当君士坦丁改信基督教并奉其为国教之后,对性犯罪
和道德犯罪的惩罚比以往严厉了许多。昔日私下里的小过错成了要被公
之于众的罪行,且常常受到残酷的惩罚。以往,通奸者可能会被流放至
孤岛;但在基督教帝制时期,各类伤风败俗的性犯罪,包括通奸、兽
奸、乱伦和同性性行为,都成了死罪。不过,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对性
犯罪不再从轻处罚的现象,与其说仅仅是朝着古代《圣经》式处罚的转
变,倒更有可能是对一系列强奸和绑架案的回应。彼时,有些野心勃勃
的古罗马人试图用性侵行为达成与富家女性结婚的阴谋。[14]
无论如
何,与过去相比,将通奸、淫乱定为死罪的做法是一次明显的转变。在
古罗马帝国初期,通奸的定义为与“体面的已婚女性或寡妇”或“未婚且
不以卖淫为业的自由女性”发生性关系。[15]
对此的惩罚通常是剥夺已婚
女性的一半嫁妆以及三分之一的其他财产,并将其放逐到岛上,她的情
夫也会被剥夺一半财产并放逐到另一座岛上。涉案女性的父亲有权杀死
自己的女儿及其情夫,但前提条件是要在他女婿的家中当场抓奸,并将
他们双双杀死,一如戏剧中的情节。否则,如果做父亲的只杀了女儿的
情夫,就会被控谋杀。从本质上说,这个规定是为了防止被戴绿帽子的
丈夫及其家人不将案件移交法庭而自行实施报复。
或许早在公元3世纪初,当两名士兵因与一名女仆发生性关系而被
定罪时,马克里努斯皇帝(Emperor Macrinus,217—218年在位)就已
为后来的基督教式惩罚开了先河。由于这名女仆身为娼妓,士兵们的行
为本不触及通奸法令,但仍遭到了审判。皇帝命令划开两头阉牛的身体,趁牛还活着的时候把这两名士兵分别塞进牛身里,只把脑袋露在外
面,以便他们能相互交谈。根据一名历史学家的记载,由于他们的行为
并没有实际违反任何法律,因此受到了从任何书本里也找不出的“独一
无二的惩罚”。[16]
作为罗马法的基础,十二表法直到近10个世纪之后才被查士丁尼的
《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取代。在尤里安大帝(Emperor
Julian)治下,罗马法发展到了顶峰。此时的罗马法将1000年的法律实
践整合进条理清晰的系统中,兼顾了简明与公平。这部法典是后来大多
数欧洲(及其殖民地)民法典的基础。然而,正如一名法律历史学家指
出的,其中的刑法部分“仅仅是以一种异常古怪的形式影响了现代欧
洲”。[17]
无论如何,527—565年查士丁尼的统治标志着由古代向中世纪
的转型,他所开启的时代将一直延续到现代欧洲的诞生。[18]
但古罗马
文化早在中世纪欧洲国家成形前就将土崩瓦解。
随着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日耳曼部族,也就是古罗马人
所说的那些生活在古罗马帝国之外的蛮族,以国家的形式登上了世界政
治的舞台。日耳曼部族是早期欧洲律法汇编的重要催化剂。在欧洲大
陆,法兰克人在北高卢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西哥特人在西班牙建国,东
哥特人在意大利建国,勃艮第人在高卢东南建国(不久就被法兰克人征
服),汪达尔人则在北非建国。其中,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
贡献了最有实质意义的法律材料,且相互之间影响颇深。截至目前,后
期日耳曼部族最重要的法律文件正是出自法兰克语文献,且被认为是除
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典之外的所有蛮族法律中最具日耳曼特色的。[19]
在这些法令中,最著名的当属6世纪第一个10年间编纂的《萨利克法
典》(Salic Code)。彼时,法兰克人在北高卢建立了存续时间最长的
蛮族王国之一。法兰克法律是受古罗马影响最小、最具日耳曼特色的部
落法典。与罗马法不同,该法典没有关注婚姻、家庭、遗产、赠物和契
约,而是为诸如杀害女性和儿童、“击打头部致头颅破碎”或“未经马主同意私自剥死马皮”等各种危害行为确立了固定的货币处罚和其他类型
惩罚。《萨利克法典》中有很大篇幅涉及暴力犯罪、杀人和偷盗。我们
从法典中可以确知,一个人的财产及其本人皆可被当作犯罪赔偿的最终
抵押物,而罚款则适用于偷盗“蜂群、狗、牛、家禽、山羊、绵羊和奴
隶”的行为。通常情况下,自由民可以支付罚金,而犯了偷窃罪的奴隶
则会被处120鞭甚至阉割之刑。
《萨利克法典》的一大特色在于量刑完全取决于身价,即依受害者
和罪犯的身份来确定罚金,该制度后来在公元5、6世纪时被德国入侵者
带到了英国。每个人都有其“身价”。比方说,如果任何人杀了为国王效
力的人,会被罚24000第纳尔;如果杀了一名法兰克自由民或受《萨利
克法典》管辖的野蛮人,会被罚8000第纳尔。如果所犯罪行是暴力袭击
的话,具体处罚取决于攻击的程度和涉及的人员。根据《萨利克法
典》,“如果任何人殴打另一人的头颅导致头顶的三块颅骨破裂、脑浆
毕现,袭击者将被罚1200第纳尔”。如果有人被打断肋骨“造成开放性伤
口并伤及内脏”,相应的罚款是1200第纳尔;如果只有血“滴落在地
上”,罚金是600第纳尔。若是奴隶犯法,惩罚要严厉得多。奴隶若偷盗
价值2第纳尔的物品,一经发现,不仅要赔偿,还要被按在地上打120
棍;若偷盗价值40第纳尔的物品,则会被阉割或判罚6先令。[20]英国普通法传统
从5世纪中叶到6世纪中叶,英国受到来自北海对岸的日耳曼和斯堪
的纳维亚移民的侵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盎格鲁部族、撒克逊部族
和朱特部族逐渐融合,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事实上,英格兰
(England)这个名称正是得自“盎格鲁人的土地”(Land of the
Angles)。在这片昔日古罗马帝国的北部边陲,400年来古罗马推行基
督教的失败尝试几乎未留下任何痕迹。公元410年,古罗马军队撤离,罗马法典也从当地人的记忆中随之消散。从彼时直到1066年诺曼人入侵
前,日耳曼传统给英国地区的犯罪与惩罚制度带来了最强烈的冲击。同
彼时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最根本
的法律思想之一是人皆有价,即“身价”。有100多条法律条款列举了各
类罚金,涉及从谋杀到点滴不和的方方面面。法律规定了身体每个部位
的价值,比方说一只眼睛值半个人的身价;损坏一颗牙的赔偿是16先
令,但后臼齿只值半价。打一拳赔偿3先令,扇一巴掌则是两倍赔偿。
在大多数人看来,被掌掴的人既受了侮辱又受了伤害,可谓双倍倒霉。
到了7世纪,英国成了武装贵族精英领导下的诸多小侯国的大杂
烩,基督教得以在此生根发芽。星罗棋布的小王国起起落落,直到公元
9世纪初才出现了若干个较为稳定的国家。在此期间,为了避免暴力循
环和世族仇杀,法律规定对杀人罪的惩罚是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赎罪金。
梅特兰(Maitland)和波洛克(Pollock)在其关于英国法律史的经
典著作中指出,日耳曼入侵者“不擅文字”,且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时
代也不甚清晰。[21]
约公元6世纪的根特王埃塞尔伯特(Ethelbert of
Kent)颁布律法——当时的人们称为法令——是第一部日耳曼成文法,其中大部分涉及暴力犯罪和牛马盗窃罪。除了规定身价金,这部盎格
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法典也采用了一些监禁方式来处罚偷盗、行巫术之类的罪行,但最常见的刑罚仍体现了欧洲大陆特色,比如断肢、死刑
或放逐。自5世纪起,绞刑成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英国的主要处决方
式。绞刑作为主要的处决方式被一直沿用到20世纪,尽管在诺曼时代早
期曾短暂地遭弃。在诺曼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执行绞刑的过程毫无技
术可言,受刑人得被慢慢勒死,而不是利用身体下坠时的重力和绞索结
折断脖颈子速死亡。从缓慢勒死到利用位于绞索结折断脖子,这个较人
道的方法改进花费了刽子手们几个世纪的时间。
在现代刑法制度出现以前,几乎不存在什么审判程序。影响了日后
正式审判程序的大量实践均来自欧洲诸日耳曼王国,例如神裁和辩护
人,也就是誓言帮手(愿意为你的人品发誓担保的人)。上述这两种做
法均来源于这样一个信念:上帝将站在正义的一方。自从日耳曼部族将
这些基于上帝审判的做法从欧洲大陆带到英国,直到1066年诺曼人入侵
之前,当地人一直依靠这套简单易行的方法进行裁决。
正如前一章所述,回顾历史,在不同的社会中,我们都可以见到某
类神裁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用火或水来审判在英国最常见,且审
讯通常在牧师的协助下完成。曾经做过伪证或无法提供足量誓言帮手的
罪犯必须接受神裁。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13世纪,其理念基础在于相信
上帝会保护无辜者。在实践中,神裁是终极审判,人们希望罪犯能在走
到这一步之前就坦白。火审有若干形式。有时候,被告要被蒙住眼睛走
过滚烫的木炭或炽热的金属。有时候也会用“浸锅法”,要求被告将手伸
进盛着沸水的大锅,并从锅里取出一块石头或约1磅(约0.45公斤)重
的东西。如果被告的手或脚在神裁三天后依旧化脓未愈,则被判有罪。
在另一些情况下,被告会被投入水中,沉下去就是无辜,浮上来是有
罪。杀人、伪造、行巫术、信奉异端邪说等罪行往往会用这种方式审
判。
判定有罪或无辜的第二种重要方法是使用誓言帮手。在这种情况
下,原告和被告都要提供誓言帮手来担保本方主张的真实性。誓言帮手的人数取决于身份等级和案件的严重程度。那些拒绝进行宣誓采证、神
裁或拒绝连续四天出庭的人会被剥夺法律权益,也就是说他们将不再受
到法律保护,可以被追杀。剥夺法律权益的手段可以适用于回避司法机
构、拒绝支付罚金、拒绝出庭或潜逃的人。此外,这些人也会被剥夺所
有财产和公民权利。梅特兰和波洛克把剥夺法律权益称为“野蛮时代的
死刑”。[22]
一旦失去法律权益,一个人注定会同他所在的社群发生冲
突,而周遭的人也会攻击他。在13世纪以前,驱逐被剥夺法律权益的
人,焚烧其住所,毁坏其田地,对其追杀到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
有些罪行,比如叛国或暗杀,是罪无可恕的,除非被告能提供足够
多的誓言帮手或通过更严苛的神裁考验,比如从沸水中取出3磅(约
1.36公斤)重物(而非通常的1磅)。此外,常规神裁中要求沸水没过
手腕,更严苛的神裁要求沸水没过手肘。未能通过神裁意味着将被处
决。而在诬告、习惯性犯罪等较轻的案件中,未通过神裁的人将被判断
肢刑或肉刑。
日耳曼部族钟情“容易辨识的”惩罚手段,比如对诬告者割舌,对发
伪誓者斩断右手。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前,盎格鲁-撒克逊的主要刑
罚包括绞刑、火刑、溺毙、石刑、深坑处决、割耳、削鼻、割上唇、剁
手、剁足、宫刑、笞打和卖作奴隶。有趣的是,以囚禁为目的的建筑未
被提及。或许,正如梅特兰和波洛克指出的:“对于一个没有监狱和收
容设施的国家而言,最简单的惩罚方式就是处死。”[23]
根据6世纪的《埃塞尔伯特律法》(Laws of Ethelbert),逃犯在特
定条件下可以向教堂寻求庇护,这些条件包括向神职人员忏悔罪行、交
出所有武器、向教堂支付费用、坦白犯罪细节。罪犯可以得到40天的庇
护,之后要面见coroner
[24]
并发誓从此流亡。在离开故土的过程中,罪
犯会被安全地指引到最近的海港。不同于被剥夺法律权益者,自愿流亡
者可以穿着白袍,带着木十字架,以免受各种侵害。但流亡者一路上不得在任何地方停留超过两晚。到了16世纪,亨利八世要求给流亡者打上
易于辨认的烙印,以防这些人在没有得到宽恕的情况下返回英格兰。这
项规定在诺曼时代剩余的时间里一直得到奉行,直到1623年被国王詹姆
士一世废止。
公元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循着残暴的丹麦维京海盗的航迹,在从泰晤士河一直延伸到利物浦的一片被称为丹麦法区的地方安了家
(也将“法律”这个词引入了英语词典)。他们带来了具有浓厚的斯堪的
纳维亚宗教色彩的风俗,比如将罪犯勒在长木棍上并反复扎刺直至其死
亡。这个向奥丁表达敬意的习俗称为galgatra,或称绞刑树。在随后的
一个世纪里,斯堪的纳维亚移民与附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混杂,其各自的律法和制度也相互融合,形成了英国文化。
英国历史以及普通法传统形成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是居住在法国北部
的诺曼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格兰的入侵。1066年,威廉一世、诺
曼底公爵的军队在黑斯廷斯战役中大获全胜,完成了对英格兰的征服。
按照当时的传统,被征服地的民众通常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
为了赢得新臣民的支持,威廉一世顺势而行,沿用了大部分盎格鲁-撒
克逊司法制度,同时又从欧洲大陆引入了诺曼习惯法。他最突出的一项
改革是采用断肢刑而避免死刑。在此后的40年间,绞刑一度销声匿迹。
不过,这项措施未能防止大量罪犯在被挖眼或阉割后死亡。
诺曼人带来了很多新元素,其中包括设立治安官、coroner、法警、太平绅士和执行官职位,这些革新后来成了刑事审判体系中家喻户晓的
部分,并影响着英国普通法传统。比如1194年开始设立的郡级coroner一
职,负责调查死因可疑的案件和入室案。最早记载于拉丁文和法文史料
的宵禁在当时已存在了数个世纪,成为上等阶层限制下等民众活动的主
要手段。威廉一世则赋予了宵禁更神秘的色彩,用它来防范时刻存在的
火灾隐患。在那个广泛使用木材的世界里,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预防措
施。但事实上,这一手段更有可能是为了防止盎格鲁-撒克逊反叛者利用寒冷的夜间时光秘密集会。每晚8点,当宵禁钟声敲响时,所有的火
都要熄灭,违者将面临严厉惩罚。
诺曼人还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裁定有罪或无辜的各种方式之外增加
了一种新的神裁方式——决斗审判。早在诺曼人攻占英格兰之前5个世
纪,决斗——源于拉丁词语duellum(两个人之间的战争)——在日耳
曼勃艮第人中就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传统。用一名先王的话说,“每个人
都应时刻准备用剑来护卫他所坚持的真相,并服从上帝的裁决”。决斗
规定允许神职人员、女性和残疾人雇用代理人或帮手出战,只要他们发
誓不使用魔法或毒药。在大多数情况下,上等人使用马上决斗,下等人
则徒步决斗。如果被告能在决斗场上从日出坚持到日落,就会被裁定无
罪,原告会被绞死。在1096年的一起著名的决斗审判中,原告控告伊尤
伯爵密谋反叛国王威廉二世。国王本人亲临现场。伯爵决斗失败,被处
阉刑并挖去双眼。对决斗场地进行改进之后,比武审判变得更加实用,且规定不再允许雇用代理人。如果一名女性在审判中要对战一名男性,该男性必须站在齐腰深的坑里,该女性在坑外用拴着石头的皮带进行攻
击,男性则用棍棒还击。如果该男性三次未能击中女性,就意味着该女
性是无辜的。[25]
诺曼人攻占英格兰100年后,英格兰的犯罪问题越发严重。于是,亨利二世于1166年颁布《克拉伦登敕令》(Assize of Clarendon),建立
了大陪审团制度。陪审员要提交本地所有已知的罪犯名单,对他们进行
拷问。一旦被判定有罪,罪犯将受到严酷惩处,以儆效尤。所有没能通
过拷问的人都会被处以绞刑,或被砍掉一只脚并流放40天。10年之后,也就是1176年,《北安普敦敕令》(Assize of Northampton)规定了更
为严厉的刑罚,包括(在拷问定罪之后)砍断右手和右脚。
《克拉伦登敕令》也极大地促进了监狱建设。威廉一世是这一变化
的引领者,在他的推动下,英国修建了第一座皇家监狱——伦敦塔。不
过,这座监狱主要是用于关押国王的敌手。除伦敦塔之外,当时还有另几座专门羁押所。到了亨利二世时期,《克拉伦登敕令》要求治安官在
各郡修建监狱,关押所有等待皇家巡回法官审判的重犯。自13世纪后期
以来,随着监狱的增加,被处监禁的罪行种类也越来越多。
被誉为“普通法之父”的亨利二世设立了巡回法官一职。这些法官定
期巡视英格兰各地,通过使用标准程序处理案件,旨在最终让“普通
法”通行于全国。与大多数前现代法律传统一样,习俗曾在英国各地的
地方法庭裁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地理因素和涉案人的社会地位千
差万别,它们常常给法官带来困扰。在随后的几年中,基于国王法庭大
法官裁决的法体日趋成形。渐渐地,这些法律,或称普通法,与丹麦、日耳曼法律主导的那些地区的法规形成了明显差异。随着新判例的增
加,法官们开始引用类似判例作为参考。这种做法确立了先例在审判中
的重要性,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统一的规则,它们不仅适用于英国,也适
用于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国家。伊斯兰法律传统
7世纪下半叶,与条顿蛮族入侵盎格鲁-撒克逊英国大约同一时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作为罪与罚这一主题的后来者,其后几个
世纪里形成的伊斯兰法律传统在随后的1400年间逐渐传播至北非、中亚
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地区的大部分惩罚主要遵循
同态报复的原则,“很好地满足了游牧社会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需
要”。在没有法律体系和国家概念的环境中,亲族协同成了社会最强有
力的纽带。先知穆罕默德出生于约公元570年,公元610年左右开始传
教,但伊斯兰律法直到公元8世纪才开始形成。[26]
早期的伊斯兰律法在
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阿拉伯文化的遗产。与摩西律法相似,伊斯兰法律传
统也是一种神权法律体系,基于神通过圣典授法于先知的信仰。不过,犹太律法的发展从未能达到伊斯兰律法的程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
于犹太人屡屡被监禁和驱逐的命运。
根据伊斯兰律法,犯罪指的是“行被禁之行或疏于应尽之责”。[27]
这个定义与西方实证法中的定义“违反公法并会受到以国家名义实施的
惩罚的主动行为”[28]
差不多。伊斯兰的司法实践始终强调双重保护,既
尊重被告人权利,也重视对社会的保护。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发生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前的一个现代案例来说明。一名索马里军阀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命人把失手杀死了一个平民的士兵送到受害者家
中,“迅速对其头部开枪”。军阀无意间对采访者说道:“这是伊斯兰法
律。这让公众满意。”[29]
伊斯兰法律传统最重要的两个来源是《古兰经》中的伊斯兰教法
(Sharia)和圣行(Sunna)。被视为“《古兰经》外经”的圣行由阿拉伯
习俗和先知的生平事迹构成。伊斯兰教法则是来自真主的不容亵渎的律法。从西方观点看来,它似乎不像法典那般包罗万象,结构上也较松
散。作为法律典籍,它的一大弱点在于,既然是真主所定,那就既不能
改变亦不能增补。此外,由于《古兰经》刑法的形成年代太早,如果想
适用于当代的刑事审判,即便绝非不可能,也有相当难度。
诠释先知遗训的任务落在了乌力马(ulama,或称法律专家)的身
上,他们自中世纪起就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一点同基督教的
神职人员没什么不同。公元900年,乌力马认定伊斯兰教法是完备的,无须再做更多的诠释。人们很难概括伊斯兰律法的发展,原因之一就在
于,穆罕默德死后的若干世纪里出现了四大伊斯兰法律学派,每一派都
对法律做出了不同的诠释。这四大学派各自以其创始学者的名字命名,有的宽容开明,有的则坚持宗教激进主义。这其中最开明的当属哈乃斐
学派(Hanafi),他们意识到,社会在改变,创造各种法律的环境也在
改变,因此“律法并非不可改变”。发源于伊拉克的哈乃斐学派在漫长的
奥斯曼人统治期间因诠释律法而声名卓著,它也是如今印度大部分地
区、巴基斯坦以及除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其他几个中东国家的官方学派。
态度最严格、最保守的是罕百里学派(Hanbali),它对其余三派的任何
创新都一概反对。该学派如今活跃在沙特阿拉伯。
在穆斯林刑法中,罪行分成三大类,相应的惩罚是由《古兰经》确
定还是由法官决断各有不同。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须给予强制惩罚,因
此适用罚戒重罪的伊斯兰教法,且不得宽恕、调解或开脱,相应的惩罚
也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行的规定。对罪犯的惩罚方式以肉刑为主,但与终身监禁和西方国家使用的其他惩罚手段不同,伊斯兰教法的行刑
过程迅速、公开,且只给罪犯带来短暂的痛苦。[30]
比如,若窃贼被判
削手,医生通常会事先为他们施麻醉,然后用利刃行刑。究竟何种罪行
要依伊斯兰教法判决,目前并没有共识,但绝大多数资料显示,伊斯兰
教法涉及的罪行主要包括通奸、偷窃、抢劫和诽谤、通奸或发生非法性
关系,也就是主动与配偶(无论是否已婚)之外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
不过,近来伊斯兰教法已对涉案一方是否已婚做出了区分。若性接触的程度仅限于男性器官插入女性器官,具体惩罚可依情酌定。正如上一章
提到的,各社会十分重视保护和维护信众中清白、高尚的血统。有罪一
方的身份不同,犯通奸罪的惩罚也不同。通常,对已婚者的惩罚是石
刑,对未婚者则处100下鞭刑。
关于伊斯兰法律传统中的石刑,在此有必要附上一笔。与伊斯兰法
律本身一样,石刑基于早前的习俗,尤其是《旧约》里提到的摩西用石
刑惩罚不守安息日的人。从公元1世纪起,犹太教法将石刑定为对一系
列违法行为的惩罚手段,并详细规定了行刑方式。不过,对于石刑究竟
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应用,我们只能凭借推测。
石刑并没有记载于《古兰经》,但出现在关于伊斯兰律法传统的圣
言录中,并被明确规定为对通奸行为的惩罚手段。直到2007年,伊拉克
库尔德雅兹迪教派聚居区仍有石刑处罚的案例。西方人或许认为石刑野
蛮残忍,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石刑符合穆罕默德时代阿
拉伯社会的价值观。纵观历史,人们在实施刑事处罚时往往雷声大雨点
小,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警告”,而非结结实实的惩罚。
不经允许转移他人财物并意欲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偷窃。该类行为的
严重性通常取决于偷窃的价值和手法。尽管如此,伊斯兰教法规
定:“偷窃者,无论男女,一律砍断双手。”为了起到震慑作用,行刑通
常公开进行。不过,被窃物品应具有最基本的价值,如果偷窃的是酒、猪肉等在伊斯兰教义中毫无价值的东西,则无须受断手刑罚。
抢劫,即武装抢劫或拦路抢劫,由于使用了强迫和埋伏手段,被视
作更为严重的罪行。《古兰经》对此类罪行的惩罚是“处死、钉十字
架、手脚交互割去(交叉断肢)或驱逐出境”。有一种司法解释认为,法官在判决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罪行的严重程度决定具体
的惩罚手段。但大多数解释认为,实施何种处罚完全取决于罪行的严重
程度,法官并没有自由裁量权。杀人者将死于剑下;偷窃者将被交互断
肢(斩断右手和左脚);使用暴力威胁但并没有杀人或偷窃的,被处驱逐出境(或监禁);同时犯有偷窃和杀人罪的将被钉十字架。同斩首一
样,断肢刑也用剑或弯刀执行。不过,关于钉十字架的方式仍存在争
论。大多数人认为,抢劫犯会被活生生钉上十字架,然后用长矛刺死。
另一些人则认为,罪犯会先被处决,然后尸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三天,任
凭风吹日晒,以此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和震慑。既谋财又害命的土匪将
被斩首,陈尸十字架。如果仅仅杀了人但没有偷窃,则判单纯斩首。总
之,侵害商贸和旅行的行为绝不能轻饶,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相应的刑
罚如此严酷且要公开进行。
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第四种罪行是诽谤,也就是诬陷他人有不道德行
为。要证明一起通奸案,必须有四名男性证人对目击的情况做出清晰描
述。如果其中三个人的证词对被告不利,但有一名证人不能证实该行
为,则另三人将受惩罚。比如说,若一名女性被控通奸,但控诉人无法
依照法律要求提供四名证人,便属于诽谤。对诽谤罪的惩罚是鞭打80
下。
归属于同态复仇类惩罚的罪行,或称“血腥”犯罪,通常是指有意或
无意地伤害他人的躯体。和这个概念相似的现代法律术语是“人身伤害
罪”,包括谋杀、主动或被动杀人、故意或非故意的人身伤害、致人伤
残。对此类罪行的惩罚有两种方式。同态复仇惩罚只适用于针对人身的
故意伤害,且需证据确凿。同态复仇在伊斯兰教法中由来已久,目的是
要满足受害者及其家人寻求报复的普遍心理,同时避免报复过度,不致
引发世仇和更多暴力。在此情况下,同等程度的复仇是被法律允许的,这与《汉穆拉比法典》以及后来的希伯来法律中感同身受、刑同其害的
原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回事。但与《汉穆拉比法典》不同的是,根据伊
斯兰教法,如果有人放火烧了他人的房屋,受害人不能用同样的手法实
施报复,否则便会受到处罚。另一种惩罚方式是支付赔偿金,即向受害
者或其家庭支付赔偿,该方式适用于非故意伤害罪,包括被动杀人和非
故意伤害。最初,赔偿金的数量是一定的,不依社会经济地位而变。大
部分学者认为,对女性的赔偿金是男性的一半。按照举证要求,使用赔偿金惩罚之前必须证明被告人神志清醒且做出犯罪行为时是出于自愿。
因此,想寻求同态复仇的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做出适宜
的复仇行动,否则就要由专业行刑者代劳。同态复仇的限度在于施予罪
犯的痛苦不能比受害人遭受的更大。如果缺少确凿证据,则只能适用赔
偿金处罚。
第三大类,也是最轻的一类是可判酌定刑的罪行,主要指的是《古
兰经》或圣行没有规定惩罚方式的犯罪行为。有阿拉伯学者认为,酌定
刑惩罚比伊斯兰教法或同态复仇规定的惩罚更严厉,因为后者有预先规
定且惩罚是有限度的,而酌定惩罚则完全由法官决定。在此方式
下,“一个人有可能被反复鞭笞,直到完成必要的忏悔或赎罪”。[31]
可
处以酌定刑的罪行包括小偷小摸、通奸未遂、同性恋行为、强奸以及其
他伊斯兰教法禁止但并未规定相应惩罚措施的行为。因此,对被控吃猪
肉、做伪证、放高利贷、饮酒、在秤上做手脚者的惩罚各有不同。既然
惩罚方式由法官或统治者决定,他们就要首先考虑罪行的严重性,然后
考虑罪犯本身的人品、犯罪记录、生活方式和最终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此类罪行很少会被处死,但遭鞭笞极为常见,这对罪犯本人和社会都是
最好的选择。鞭刑受青睐的原因在于执行迅速,能让罪犯——通常是其
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返回工作岗位养活家人。不使用监禁手段,罪
犯的家庭就不会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罪犯个人也不会受到监狱里其他
罪犯的负面影响。鞭笞刑的下限是三鞭,上限说法不一,但通常为39至
75鞭不等。有一则故事或许可以说明法官在处理酌定刑时如何灵活地行
使自由裁量权。也门的首任总督用葡萄酒招待宾客,然后对那些喝醉了
的人提起控诉。当客人们提出抗议时,他解释说:“我惩罚的不是饮
酒,而是醉酒。”哈乃斐学派只禁止饮用葡萄酒,因为那是先知时代唯
一可得的酒类,其他种类的酒精(或毒品)只要不至于使人沉迷,就未
必会被禁止。
就很多方面而言,酌定刑似乎更现代。某些行为并没有相应的具体
惩罚,但这些行为的确不是穆斯林应有之举,酌定刑的运用使得伊斯兰教法既可以“发展并应对现代生活的新需求”,同时仍然能满足穆斯林社
会的要求。调和中世纪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之间差异的困难可以从最近的
一个案例中窥见一斑。一名沙特女性因违反本国禁止女性驾车的禁令被
判鞭笞10下。作为全世界唯一不允许女性开车的国家,那里的很多家庭
被迫雇用驻家司机。然而每月至少300美元的额外开支超出了大多数家
庭的经济能力,因此女性不得不依赖男性亲属送她们上学、就医和购
物。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没有成文法规定女性不得开车,但按
照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有必要设立限制自由和活动的禁令,从而让女
性远离罪恶。抗议者指责当局因驾车鞭笞女性,因为对交通违法行为的
惩罚至多不过是罚款而已,于是有人说:“就连先知的妻子们也骑骆
驼,骑马,因为那是唯一的通行方式。”在此要为警方辩解的是,尽管
警方的确会拦下开车的女性,但通常只是询问而已,并在她们签署不再
开车的保证书后便放行。巧的是,那名被判鞭刑的女性当时正在参加一
场有组织的抗议活动,因此这顿鞭刑有可能是来自宗教强硬派的报
复。[32]现代世界的伊斯兰教法
从现代观点来看,保守的伊斯兰法律往往被视为既严酷又不合时
宜。这主要是因为现代政权抛弃了伊斯兰法律中的实证思想,背离了伊
斯兰教义和精神。不幸的是,在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苏丹、尼日利亚和阿富汗这些用伊斯兰律法取代了更开明的世俗法律的国家
里,伊斯兰教法中不太人道的一面愈演愈烈,尤其是有些惩罚的确源自
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刑罚体系。石刑是这一类惩罚中最常被提及、最
容易被误会的一种。伊斯兰法律和其他习俗的设计初衷是要保护男性血
统、家庭、荣誉和财产。在部族社会里,族长掌握着孩子的血统关系。
性犯罪之所以要被处以石刑(而非其他形式的处决),乃是因为人们认
为此类罪行辱没了族群的血统,因此要由部族成员共同惩罚。与其他惩
罚手段不同,被家人、旧日好友和邻居在大庭广众之下用石头砸死,对
罪犯而言一定相当可怕。人们希望这样的判决能够杀鸡儆猴,减少引发
亲子关系问题、威胁部族血统完整的犯罪行为。
以下是伊斯兰教法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几个应用案例。伊朗的伊斯兰
教法禁止放高利贷行为,任何放贷牟利的人都会被判处74鞭以及最长3
年的监禁。此外,法令还规定,初犯者要被剁掉右手的4根手指,再犯
者剁掉脚趾,第三次犯则要被终身监禁。一个案例体现了同态惩罚的持
久影响力。2011年,一名伊朗男子因将一桶硫酸泼在一名拒绝与他结婚
的女性脸上而被定罪,并被判以相同的方式弄瞎双眼。[33]
此案发生在
2004年,受害人在攻击中失明,容貌被毁。她有权宽恕攻击者,但她不
顾国际人权组织和英国政府的呼吁,拒绝原谅他的罪行。她的理由是,惩罚乃是对其他打算做类似行为的人的警告。2008年,伊朗的一个法
庭“同意受害者的要求,依据伊斯兰法理允许受害者向罪犯寻求报复”,下令在该犯的每只眼中滴入5滴相同的化学品。只有受害者本人才能以宽恕罪犯的方式阻止判决。[34]
沙特阿拉伯仍使用斩首作为处决方式,侨居利雅得的外国人把行刑
的地点译作“咔嚓咔嚓广场”。在那里,刽子手用4英尺长的弯刀公开行
刑,血水通过一个小小的金属阴沟盖流进下水道。
1983年9月的一天,气温一如往常达到近38℃,数千名苏丹人聚集
在喀土穆城北一所监狱的庭院内,焦急地等待观看伊斯兰式行刑。两名
因偷窃获罪的男子坐在椅子上,脸上蒙着白布,准备接受传统惩罚。行
刑前,焦躁的人群聆听了对这两人的指控。《古兰经》中关于非法占有
的韵文被大声念诵,人群齐声高呼:“真主是伟大的!”接着,持刀的行
刑者出现了,麻利地砍下了两名罪犯的右手。令人惊讶的是,罪犯几乎
没有流多少血。观察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们的上臂扎了止血带。对于其
中一名罪犯而言,这还不算完。此人是尼日利亚移民,下个月,他还要
被砍掉一条腿。[35]
1996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个伊斯兰教法庭判决一名菲律宾女
佣受罚100鞭,罪名是她刺死了雇主。鞭刑分5天进行,每天执行20鞭。
当地官员说,这只是象征性的惩罚,行刑者在胳膊下垫了一本书以减轻
抽打的力度。尽管女佣声称前雇主企图强奸她,自己只是在自卫,但仍
免不了被判鞭刑并处一年监禁,之后被驱逐出境。
有很多伊斯兰教法的支持者将本地的低犯罪率与非伊斯兰教法地区
的高犯罪率对比,声称这是伊斯兰律法的功劳。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
为这些国家的犯罪数据很少拿出来与世界其他地区共享。不过,有一个
地方的确可以体现出伊斯兰教法的作用,那就是1996年的索马里。当
时,摩加迪沙(Mogadishu)到处都是家族仇杀、强奸、抢劫以及——
用一名《纽约时报》记者的话说——“宛如世界末日后的”随意杀人。走
投无路之下,一所伊斯兰教法法庭临危受命,将首都部分地区由“无法
无天之地变成了相对安全、文明的区域”。如果说有人对平息犯罪潮的方法有任何质疑的话,那主要是针对砍掉本地窃贼手足(在不使用麻醉
的情况下公开行刑),并置于本地体育场前示众的做法。[36]
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间,塔利班用伊斯兰法律的
极端版本完成了“自我定义”。随着该组织在阿富汗的壮大,他们也向世
人展现了自己的伊斯兰法律。与大众认知相反,在20世纪90年代塔利班
上台之前,对通奸犯行石刑的做法在阿富汗并不常见。而那些确实使用
石刑的案例均有严格的宗教监督,且首先进行了公正的审判,并由宗教
学者为惩罚设定限制。按照规定,石头应体积较小,参与行刑的人在投
掷时手臂抬起的高度不得超过头。最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合法的法庭来
完成。在2010年的一起案件中,一对夫妇因私奔被石刑处死,行刑地点
位于一个村落里,没有政府监督。一名教派长老指责这起石刑违法,指
出“用大石头非法处决是错误的”。[37]
在2010年的一起案件中,昆都士省(Kunduz Province)的数百名村
民参与了处死一对年轻人的石刑。但在更多情况下,尤其是如果涉事男
性属于塔利班组织或与该组织有密切关系,石刑只会落在女性身上。有
时候,同性恋会被迫站在砖墙前,被推倒的砖墙砸死。塔利班极尽严格
地践行伊斯兰教法,对宽恕问题亦不例外。1999年,一名男同性恋被判
死刑,具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2486KB,362页)。